致命流感:百年治疗史.pdf
http://www.100md.com
2020年3月14日
 |
| 第1页 |
 |
| 第9页 |
 |
| 第17页 |
 |
| 第27页 |
 |
| 第31页 |
 |
| 第114页 |
参见附件(2743KB,316页)。
致命流感:百年治疗史,流感一直在人们的生活中的致命疾病之一,流感能够快速通过人传人的形式进行传播,本书从历史来发生的重大流感事件说起,为读者更好知晓流感。

致命流感介绍
我们距1918年灾难性流感已经100周年,杰里米·布朗博士,一位医生,采访了的流行病学家、政策制定者以及率先对1918年原始病毒的遗传基础进行测序的研究人员,探究了令人不安的、可怕且复杂的流感病毒的历史,旨在提供全面综合的历史的同时,探索一条有关流感的未来路线图。本书以百年间爆发的几次严重的流感疫情为主线,讲述了人类发现流感病毒并与之抗争的历史,同时也提出并解答了一些与流感相关的问题,比如:大流感病毒起源于哪里,我们为下一次流感大流行做好准备了吗,我们应该接种流感疫苗吗,我们离找到一种方法还有多远。
致命流感作者
杰里米·布朗,一位资深的军医和急诊科医生,在伦敦大学医学院取得博士学位,随后前往波士顿贝斯以色列医院进行急救医学实习。曾任华盛顿大学急救医学系研究主任,在此期间,他带领团队建立了一套HIV的筛查程序,一种针对肾绞痛的新疗法获得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三项许可。目前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急救护理研究办公室负责人。
译者简介
王晨瑜,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学专业,硕士毕业于复旦大学药学专业,目前从事医药风险投资。
致命流感主目录
1.灌肠、放血和威士忌:治疗流感
2.流感:病毒的前世今生
3.来势汹汹: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
4.“我会死吗?”:第二轮,第三轮,第四轮...
5.复活1918年的流感病毒
6.数据、直觉和其他战争武器
7.你的晚间流感预报
8.物资储备中的漏洞:达菲和尚未发现的治疗方法
9.寻找流感疫苗
10.有关流感的商业活动
致命流感点评
1、流感是世界上致命的疾病之一,《致命流感》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述了令人无比信服的相关故事。这本书非常及时,有趣,引人入胜,发人深省。
2、布朗追溯了流感病毒数百万年的历史、人们为了解并治疗它所付出的努力,以及这种病毒的多次毁灭性爆发……这是一本扎实可靠的科普书。
3、杰里米·布朗是美国的急诊科医生,他创作了一本了不起的书。从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到近期的流感爆发,讲述了一个个扣人心弦的故事,从全新视角看待我们与流感的斗争。本书涉及广泛的研究,语调幽默,它使我们不忘现代医学已取得的长足进步,也注意到每个流感季我们仍面临的危险。
致命流感:百年治疗史截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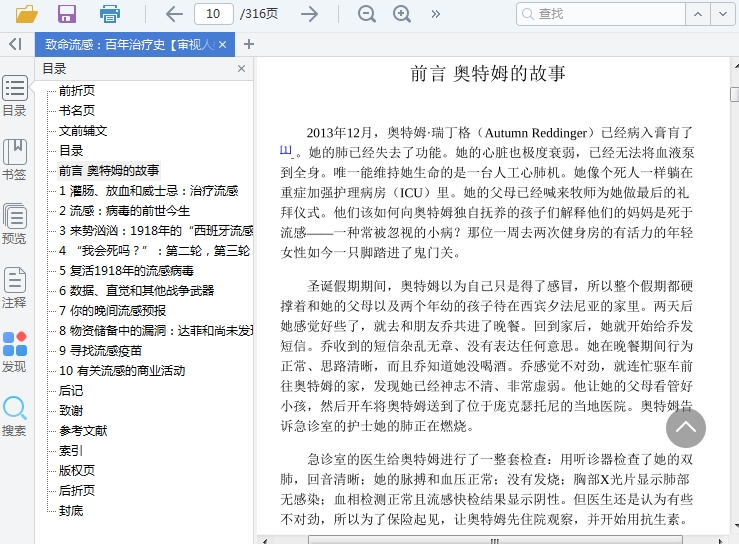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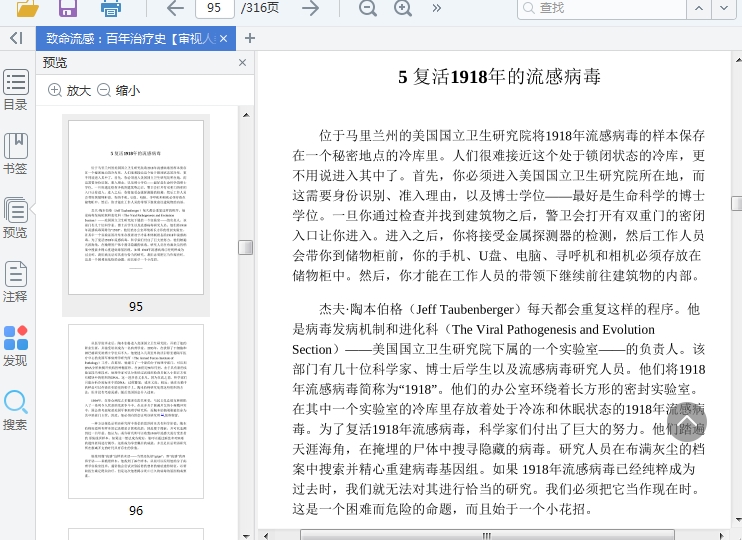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0 By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INFLUENZA:The Hundred-Year Hunt to Cure the Deadliest Disease
in History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Dr. Jeremy Brown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Touchstone ,a
Division of Simon Schuster,Inc.
我们纪念战争,但其他极具破坏性的事件也应留置于我们的集体记
忆中。这个世纪是灾难、自然灾害、世界大战、疾病以及冲突不断的世
纪,也是一个大规模扩张、融合、全球化、技术突破和取得医疗成功的
世纪。流感大流行说明了这两个问题。人们的身体处于危险之中,而大
脑仍停留在舒适区。这是人类的失败,也是人类的胜利。
——杰里米·布朗 本书作者
杰里米·布朗是美国一流的急诊科医生,他创作了一本了不起的
书。从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到最近的流感爆发,讲述了一个个扣人心弦
的故事,从全新视角看待我们与流感的斗争。本书涉及广泛的研究,语
调幽默,它使我们不忘现代医学已取得的长足进步,也注意到每个流感
季我们仍面临的危险。——盖尔·达奥诺弗里奥博士 耶鲁大学医学院急诊医学系主席
流感是世界上最致命的疾病之一,《致命流感》用通俗易懂的方式
讲述了令人无比信服的相关故事。这本书非常及时,有趣,引人入胜,发人深省。
——大卫·格雷戈里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政治分析师,前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会见新闻界”节目主持人“流感是连
环杀手”,布朗从医学史、病毒学、诊断和治疗、经济学和流行病学、卫生保健政策、疾病预防等各个角度巧妙探讨了这种病毒感染。
——《书单》(Booklist ) 杂志重点书评
布朗追溯了流感病毒数百万年的历史、人们为了解并治疗它所付出
的努力,以及这种病毒的多次毁灭性爆发……这是一本扎实可靠的科普
书。
——《科克斯书评》(Kirkus Reviews )
布朗以这部讲述医学与流感长期斗争的可靠著作来纪念1918年西班
牙大流感结束100周年。布朗叙述了20世纪90年代为再现并在基因上解
码西班牙流感病毒所付出的“史诗般的努力”,这一举措不仅引发了人
们“所有这些修补都是在制造超级病毒”的担忧,而且凸显出了流感不易
把握的特性。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急诊科医生,布朗也就对抗该病毒提
供了广泛的建议。
——《出版者周刊》(Publishers Weekly )
谨以此书纪念以下逝者和生者
罗斯科·沃恩,纽约水牛城的士兵,1918年9月26日因流感病逝于南卡罗来纳的杰克逊营地。他的献身帮我们更好地理解了让他和其他数百万人丧生的流感病毒。
奥特姆·瑞丁格,她和流感抗争的故事是关于个人勇气和现代医学努力的宝贵一
课。
为了防止西班牙流感的传播,请在手帕里打喷嚏、咳嗽或吐痰。如果人人都能把
这个警示谨记于心,那就不会受到流感的威胁。
——费城蒸汽机车上贴的标语,1918年10月
就危险性而言,没什么比流感更厉害。
——汤姆·福里登,前美国疾控中心主任
2017年1月目录
前言 奥特姆的故事
1 灌肠、放血和威士忌:治疗流感
2 流感:病毒的前世今生
3 来势汹汹: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
4 “我会死吗?”:第二轮,第三轮,第四轮……
5 复活1918年的流感病毒
6 数据、直觉和其他战争武器
7 你的晚间流感预报
8 物资储备中的漏洞:达菲和尚未发现的治疗方法
9 寻找流感疫苗
10 有关流感的商业活动
后记
致谢
参考文献
索引前言 奥特姆的故事
2013年12月,奥特姆·瑞丁格(Autumn Reddinger)已经病入膏肓了
[1]。她的肺已经失去了功能。她的心脏也极度衰弱,已经无法将血液泵
到全身。唯一能维持她生命的是一台人工心肺机。她像个死人一样躺在
重症加强护理病房(ICU)里。她的父母已经喊来牧师为她做最后的礼
拜仪式。他们该如何向奥特姆独自抚养的孩子们解释他们的妈妈是死于
流感——一种常被忽视的小病?那位一周去两次健身房的有活力的年轻
女性如今一只脚踏进了鬼门关。
圣诞假期期间,奥特姆以为自己只是得了感冒,所以整个假期都硬
撑着和她的父母以及两个年幼的孩子待在西宾夕法尼亚的家里。两天后
她感觉好些了,就去和朋友乔共进了晚餐。回到家后,她就开始给乔发
短信。乔收到的短信杂乱无章、没有表达任何意思。她在晚餐期间行为
正常、思路清晰,而且乔知道她没喝酒。乔感觉不对劲,就连忙驱车前
往奥特姆的家,发现她已经神志不清、非常虚弱。他让她的父母看管好
小孩,然后开车将奥特姆送到了位于庞克瑟托尼的当地医院。奥特姆告
诉急诊室的护士她的肺正在燃烧。
急诊室的医生给奥特姆进行了一整套检查:用听诊器检查了她的双
肺,回音清晰;她的脉搏和血压正常;没有发烧;胸部X光片显示肺部
无感染;血相检测正常且流感快检结果显示阴性。但医生还是认为有些
不对劲,所以为了保险起见,让奥特姆先住院观察,并开始用抗生素。
奥特姆的状况迅速恶化。几个小时后,她变得越来越神志不清,且呼吸越来越困难。抗生素看起来没有起任何作用。该医院的工作人员给
2个小时车程之外的匹兹堡梅西医院(Mercy hospital)打了个电话。奥
特姆现在的状况很危急。用急救车运送,风险很高,所以梅西医院派了
架救援直升机来接她。直升机将奥特姆送到梅西医院时,她已经无法自
主呼吸。注射镇静剂后,医生给她插入了喉管,并连上了呼吸机。
奥特姆被直接送进了梅西医院的ICU。到此时,她咳血,呼吸机已
经无法给她输送足够的氧气以维持生命。胸片显示她的双肺(几个小时
前还是回音清晰且看起来完全正常)已经充满了脓液和体液。医生给她
用了更多抗生素,并连上了静脉输液,以防止她的血压进一步下降。凌
晨1点,ICU团队叫来了霍特·莫瑞医生,他受过专业的急诊科医师培训
且目前专职于重症监护。他是奥特姆最后的希望。
莫瑞是一名ECMO专家。ECMO,全称体外膜肺氧合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是人工心肺机应用技术。
ECMO机器把暗黑色的血液从人体里抽出来,去除二氧化碳,注入氧
气,再把鲜红的、健康的血液输回人体内。该技术常常用于心脏或肺移
植手术中。由于奥特姆的双肺彻底不工作了,所以需要该设备替代肺功
能。
当莫瑞告知病人家属要给病人上ECMO时,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可能只有几分钟来解释操作流程并得到他们的同意。“我认为我们别无
选择,”他说,虽然他非常小心谨慎,“ECMO或许可以挽救她的性命,但也会带来一系列副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家属往往很难做出明智的决定,他们往往高度依赖
医生,希望他能够告诉他们该怎么做。奥特姆的父母已经到了梅西医
院,同意ECMO计划。
很快,莫瑞将一根粗大的针头插入奥特姆的腹股沟血管中,将她的血液从体内引出,并送入机器清洗(去除二氧化碳),然后注入氧气;
另一根针头插入颈部血管,血液从此处回流到体内。ECMO能改善她体
内的含氧量,但并未持续很长时间。最后,她的心跳还是停止了。
莫瑞和他的团队(包括护士和医生)开始连续的胸外心脏按压,并
注射了一针肾上腺素来帮助恢复心跳。获得了短暂的成功。但很快又不
行了,继而注射更大剂量的肾上腺素。心脏复跳,但几乎无法行使正常
的功能。莫瑞对奥特姆的心脏做了超声,结果发现它的泵血能力不足正
常水平的10%,已经无法将血液泵至全身。
对于像奥特姆现在这种状况的病人,医生们会用一个相当让人不舒
服的词来形容——“无力回天”。用客观通俗的语言讲,这个词描述了在
挽救病人的每种尝试都失败后的无力感。奥特姆正在一步步走向死亡。
即使一开始奥特姆的流感检测呈阴性,但莫瑞医生还是用更灵敏的
方法重新进行了一次检测,结果显示奥特姆感染了H1N1流感病毒,和
2009年爆发的猪流感病毒一样。在几个小时内,病毒就摧毁了她的双
肺,现在正在攻击她的心肌。原来替代了她双肺功能的ECMO机器也不
足以维持她的生命了,现在还需要承担她衰竭的心脏的工作。为实现这
个目的,这台机器需要重新插管
[2]。这就需要将奥特姆转移至4个街区
以外的匹兹堡大学长老会医院(University of Pittsburgh’s Presbyterian
Hospital),在那里心外科医生可以做这个手术。莫瑞在救护车后车厢
里陪护着奥特姆,小心监视着便携式ECMO设备。奥特姆被直接送进了
手术室。外科医生用锯子锯开了她的胸骨,在右心房(心脏的4个腔室
之一)上插入导管,并将另一根导管直接插入动脉,然后重新缝合胸
骨。她的胸部留下了一条长长的垂直伤口,两个粗管子从伤口内延伸出
来,将奥特姆与人工心肺机连接起来。这是最后的办法了,莫瑞医生已
经没有办法提供更好的设备、更好的治疗方法或更勇敢的方案。她要么
挺过来,要么死去。奥特姆的父母,盖瑞和斑比以及他们的牧师一起坐在ICU旁边的家
属室里。“我们在一起,我们为她祈祷,”盖瑞说,“然后牧师告诉我
们,她看见了两个天使,还告诉我们会逢凶化吉的。”
牧师说对了。奥特姆的病情稳定了下来。她那颗被流感病毒打晕的
心脏在几天后恢复了正常。抗生素遏制了继发性细菌性肺炎。血压也没
再出现骤降。2014年1月10日,医生为她撤去了ECMO,虽然她还是无
法说话且需要连接呼吸机。1周后,她的状况进一步改善,可以撤去心
胸外科的重症监护设备。又经过1个月的缓慢恢复,2月13日,她从长老
会医院出院了,转到了她家附近的一家康复中心。她战胜了流感,但是
现在仍然有一场硬仗要打。在ICU里待久了的患者,身体常常会变得非
常虚弱。在康复中心,奥特姆不得不再次学习如何走路、如何爬楼梯,并进行一系列她过去认为理所应当、轻而易举的日常行为。经过两周的
严格训练,她离开了康复中心,返回家中。2014年秋天,在感染流感之
后的第9个月,奥特姆重返工作岗位。她的医疗费用将近200万美元,但
幸运的是,她有完善的医疗保险,个人只需要支付18美元。
她的颈部和胸部留下了伤疤。针管刺入腹股沟静脉造成的神经损
伤,使她到现在都无法弯曲左侧踝关节,左腿有时也会麻木。但是,她
的康复是现代医学的胜利。她被救了回来,因为她靠近一家有能力为她
提供当今最先进治疗措施的医疗机构。
如果奥特姆身处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有历史记录以来最严重的
一次流感大流行,她的命运将会截然不同。那时候最好的药物就是阿司
匹林,但当时这种药刚刚发明,常被误用致命的剂量。绝望和无视,产
生了大量稀奇古怪的治疗方法——从野蛮的放血疗法到毒气疗法。据估
计,那次流感大流行期间,有5000万到1亿人丧生。在美国,死亡人数
达到67.5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死亡人数的10倍。第一次世界大战
结束时,正是流感暴发达到顶峰之时。流感是我们在某个时间都曾经历过的东西:冬天的咳嗽、发热、身
体的疼痛和发冷,持续三四天,然后就消失了。作为一名急诊科医生或
者一名患者,我既有站在床边的经历,也有躺在床上的经历。我作为一
个病人到访急诊室的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经历,就是因为患上了非常严
重的流感。我发了高烧并开始神志不清。我已经虚弱到无法喝水也无法
下床,我的身体开始脱水。但即便是现代医学——可以把我从相对较轻
的感染中救回来,也可以把奥特姆从死亡边缘挽救回来——也不是万能
的。流感仍然是个连环杀手。
我们都满怀期待,希望看到癌症的治愈、心脏病的根除。我自然也
是有这个愿望的,但是作为一名急诊科医生,我还有个更朴实的愿望:
治愈流感。我们常会不经意地把流感当成一次严重的感冒,但是在美
国,每年会有3.6万~5万人因流感而丧生
[3]。这是一个让人震惊和绝望
的数字。但是还有更坏的消息,如果像1918年流感大流行时那么厉害的
流感毒株在今天的美国传播,那可能会造成超过200万人死亡
[4]。没有
其他能够想得到的自然灾害可以匹敌,并且流感不是人类做好预防工作
就可以防止它到来的。2018年早些时候,报纸上说当年的流感季是近十
年来最严重的
[5]。常常见到报道说年轻人、原本很健康的人死于流感。
有几家医院因为流感病人的涌入变得拥挤不堪,他们不得不支起分诊帐
篷或者把病人送走。
流感肯定不是“众病之王”——这是肿瘤学家悉达多·穆克吉
(Siddhartha Mukherjee)对癌症的描述——但它却可以发生在所有国
家。从文明出现曙光至今,流感就一直伴随着我们,它困扰着地球上所
有的文明与社会。
————
自1918年以来,我们对流感的几次大流行都有近距离的接触。1997
年香港暴发的禽流感没有使太多人丧生,但这只是因为150万只被感染的鸡全部被及时宰杀。2003年,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暴发,感染了至少8000人,其中10%的感染者丧命。最近我们又遇到了
MERS,即中东呼吸综合征,在2012—2015年感染了1400人
[6]。这种疾
病通过感染了的单峰驼传入人群。(在此给读者一个免费的医疗建议:
一定要饮用经过了巴氏消毒的骆驼奶。)这些病毒性疾病都起源于动物
宿主(目前认为)
[7]
,然后以某种方式传播进入人群——这也是1918年
的情形(目前我们是这么认为的)。我们不知道下次病毒大流行会在何
时何地发生,但我们可以确定它会发生。毋庸置疑的是,如果不早做准
备,那我们将会面对一个颇为艰难的局面。
1918年那场流感大流行之后的百年间,我们对流感有了更深入的了
解。我们知道了它的遗传密码,它是如何变异的,它是如何使我们生病
的,但是我们仍然没有有效的方法去战胜它。我们拥有的抗病毒药物用
处不大,流感疫苗的保护力也有限。在运气比较好的年份里,疫苗保护
的有效率只有50%,而2018年这个有效率的数字更低。疫苗只对大约三
分之一的接种者有效。
仅仅一个世纪,我们就忘了1918年那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它
是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疫情。在这期间,我们了解和掌握的知识足
以让我们畏惧并激励我们,但可能还不足以让我们有能力去阻止另一场
流感大流行的发生。正是由于它的神秘、变异和传播能力,流感成为人
类最强劲的对手之一。1918年的经验教训可能是我们唯一拥有的可以和
死亡结局抗争的免疫力。
[1] 奥特姆与流感抗争的细节来自多个电话访谈和我在2017年12月与奥特姆本人、其父亲、其医生霍尔特·莫瑞(Holt Murray)博士的邮件往来。
[2] 即由原来的股静脉引出颈静脉泵入的V-V ECMO变为股静脉引出颈动脉泵入的V-A
ECMO,或开胸手术后从左或右心房引出泵入动脉的A-A ECMO。——译者注
[3] “Estimating Seasonal Influenza-Related Deaths in the United States”,Centers for DiseaseControl and Prevention,2018年1月29日更新,http:www.cdc.govfluaboutdiseaseus_flu-
related_deaths.htm.
[4] 对1918年美国死亡人数的预估是基于1.03亿人口死亡67.5万人,今天美国有3.22亿人
口。
[5] Donald McNeil,“This Flu Season Is the Worst in Nearly a Decade”,New York Times ,January 27,2018:A15.
[6] 世界卫生组织“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MERS-CoV). Summary
of Current Situation,Literature Update and Risk Assessment”,2015年7月7日,可以从以下网址下
载,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1791842WHO_MERS_RA_15.1_eng.pdf.
[7] SARS可能是从果子狸(Himalayan palm civet)群体中开始流行的。这是一种真实的动
物,而且在部分国家和地区被食用。给读者一个免费的建议:远离狸猫类食物。参见W. Li et
al.,“Animal Origins of the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Insight from ACE2-S-
Protein Interactions”,Journal of Virology 80,no.9 (2006):4211-19.1 灌肠、放血和威士忌:治疗流感
我有很多嗜好,爱喝鸡汤是其中最糟糕的一个。当我还是个孩子的
时候,总是期待母亲在周五晚上可以给我做鸡汤喝。时至今日,我还记
得在伦敦长大的情形,以及伦敦那漫长多雨的冬夜。几个世纪以来,鸡
汤被认为是治疗咳嗽、感冒、发烧、寒战的土方——这些都是流感的症
状。母亲总是提醒我要把汤喝完,这样整个冬天就不会生病了。鸡汤是
我们可以想得到的最鲜美的预防性药物。
许多年后,我在伦敦的一所医学院校看到了一项研究,说鸡汤可能
真的有用。这篇文章发表在1978年的《胸科学》(Chest )杂志上
[1]
,文章的标题就像鸡汤那样鲜美:《饮用热水、冷水和鸡汤对鼻腔黏液流
速和鼻腔气流阻力的影响》。
在此项研究中,肺病专家让健康志愿者选择喝热水、冷水或热鸡
汤,继而检测鼻腔阻塞程度的变化——或者就像论文标题所说的,评估
流经鼻腔的黏液或气体的速度。研究者总结道,热水有助于疏通堵塞的
鼻子,鸡汤含有“一种额外的物质”可以使通畅程度更好。没人能够说得
清到底是 什么神秘成分,但研究者推测鸡汤里起关键作用的是蔬菜和
鸡肉的营养搭配。
内布拉斯加大学(University of Nebraska)医学中心的斯蒂芬·伦纳
德(Stephen Rennard)博士已经研究鸡汤十几年了。2000年,他通过对
他妻子的立陶宛祖母传下来的食谱进行研究,发现鸡汤中含有一种抗炎
症的物质
[2]
,可以通过抑制因感染而产生的某种白细胞的活动,从而减轻上呼吸道感染症状。
“可以确信无疑的是,100年后,我所做的其他事情都可能被人遗
忘,因为它们会变得和人们的生活无关,会过时,”伦纳德博士在一条
拍摄于自家厨房的YouTube视频里说道
[3]
,“但是,关于鸡汤的论文可
能仍然会被引用。”它的功效经过了医生的检验,得到了奶奶的认可。
有时候,古老的经验会带来临床上的成功。对于其他曾被用于治疗
流感的方案或药物,我也希望如此。灌肠疗法、水银疗法、树皮疗法、放血疗法等,都是一些你想不到且让你恶心反胃的方法。值得庆幸的
是,你不是出生在20世纪初。今天,一个合格的医生不会给你用这些方
法。但是就在100年前,它们却是当时最先进的方法。更让人震惊的
是,21世纪的今天,我们自认为最先进的方法也未必比过去那些显得粗
鲁的方法高明多少。
————
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卸任总统后不到3年,就躺在了他的
临终病床上。作为最后一种挽救他生命的方法,医生们切开了他的血管
以阻止感染摧毁他的咽喉部位。华盛顿经历了4次放血
[4]
,最后一次是
在他死前几个小时。
“我要走了。”华盛顿对他的秘书托拜厄斯·李尔(Tobias Lear)说。
“他死于缺血和缺氧。”华盛顿的朋友、家庭医生威廉·桑顿
(William Thornton)说。他甚至建议通过输羊血让华盛顿复活
[5]。
放血疗法就是把人体的血液、毒素和病原体排出体外,这是两千多
年来主流的治疗方法。在任何有用的药物或治疗方法出现之前,放血疗
法几乎是当时的全部了。这种方法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公元2
世纪的希腊医生盖伦(Galen)
[6]
的著作中曾提到这是一种可以治愈疾病的重要方法。放血疗法在《塔木德》(一本记录与犹太人法律和道德
相关的辩论的著作,成书于公元600年左右)中被多次提及,在中世纪
及其之前被广泛地应用。现在全球最著名的医学期刊之一《柳叶刀》
(Lancet )就是以放血疗法的主要工具命名的。
放血疗法从未成功过。事实上,它极其危险——问问乔治·华盛顿
就知道了。但是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里,这种方法仍然被用于治疗流
感,不仅限于非主流的医生,甚至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线军医也会推
荐使用,他们看到了另一个敌人——病原微生物——正在包围士兵们。
而且,这些医生还在权威的医学期刊上撰写了他们放血的经历,包括激
进的《柳叶刀》。
1916年12月,3位英国医生在法国北部服役,此时距离1918年流感
大流行还有大约2年时间。他们描述了一场席卷整个军营并导致灾难性
后果的疾病
[7]。这就像流感病毒正在进行一场预演,准备着下一步释放
更大的破坏力。医生们确诊这次的疾病是由流感杆菌引起的。并将其命
名为“化脓性支气管炎”,医生们还描述了他们如何努力治疗一个可怜的
患病士兵的失败经历。
“迄今为止,”他们写道,“我们已经无法找出任何对疾病治疗起作
用的疗法了。”然后还写道:“静脉切开术(即“放血疗法”)并未对这名
患者起作用,可能是因为我们没能早点有效地使用这种方法。”
如果你只是快速浏览了论文,很有可能就错过了这个信息——英国
医生试了静脉切开术,即“放血疗法”,但是这种方法并未奏效——他们
认为或许是因为他们试得太晚了。两年后,在流感大流行的高峰期,另
有几位英国军医也报道了给病人放血的病例,只有这次,至少在某些病
例中这种方法奏效了
[8]。
在20世纪,并不是只有英国人还在坚持给病人进行放血治疗。1915年,海因里希·斯特恩(Heinrich Stern),纽约的一名医生,出版了他的
著作《放血疗法的理论与实践》(Theory and Practice of Bloodletting)。斯特恩反对将放血疗法用于大多数疾病,但他确信这种方法对某些
疾病是有用的。
“我提倡有条件地使用这种古老的方法,”他写道,“但我并不将其
视为万灵药。”
[9]
在将放血方法推荐为流感一线疗法的问题上,斯特恩是有点矛盾
的。但就在差不多10年后,在美国的顶级医学期刊上,医生们仍然支持
用放血疗法治疗肺炎
[10]
,而且他们深信——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
下,当“我们更为保守的方法失败后”,放血疗法会成功。
用放血疗法治疗流感最终在20世纪退出历史舞台
[11]
,但是其他的
野蛮且让人生疑的方法仍然是医学计划的一部分。
————
1914年,一个名叫阿瑟·霍普柯克(Arthur Hopkirk)的医生出版了
一本黑色封面、烫金书名的小书——《流感:历史、自然、起因和治
疗》(Influenza:Its History,Nature,Cause and Treatment )。书里推
荐了一系列怪诞的流感治疗方法
[12]。对于发烧,霍普柯克医生推荐
了“大清洗”,即泻药,换个好听的名字叫“冒泡的氧化镁”。流感重症患
者需要效用更强的泻药,如升汞,这是由氯化汞制成的。众所周知,汞
是有剧毒的。
霍普柯克1914年的著作里确实包含了一些有价值的建议。例如,在
推荐升汞的同时,他还推荐了阿司匹林——从柳树的树皮里提取出来的
物质(当然今天阿司匹林仍然在使用,只不过你可能用的是泰诺或布洛
芬)。即便这是个有价值的建议,但还是过大于功,因为别的医生并不知道如何安全地控制剂量。阿司匹林过量服用后的症状是从耳鸣开始,继而出汗、脱水、呼吸急促,严重的过量服用会导致体液涌入双肺——
和流感的真实症状极其相似——继而进入大脑,然后脑部水肿,导致意
识混乱、昏迷、惊厥,甚至死亡。在西班牙大流感期间,很多人并非死
于流感,还有些人死于阿司匹林服用过量
[13]。
在流感大流行期间,阿司匹林广泛使用,但许多医生似乎并未注意
到它的危险。在德里,一些高年资医生担心在孟买和金奈的一些低年资
医生正在错误地使用该药物。在伦敦,一个在哈雷街(Harley Street,伦敦最著名的私人诊所集中地)行医的医生正大肆鼓吹使用该药物。他
建议给患者“灌阿司匹林
[14]
,剂量是每小时20格令
[15]
,持续12小时,然后每两小时给药一次”。这是最大安全剂量的6倍,是极其疯狂的阿司
匹林使用剂量。
许多人在流感大流行期间可能因服用了超高剂量的阿司匹林而不是
因为流感本身而丧生。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但是这或许可以解释
为什么有那么多健康 的年轻人死去
[16]
——这一人群在今天看来是很少
会被严重的流感感染的。
霍普柯克也建议肺炎患者服用“一茶匙复方安息香酊(Friar’s
balsam)
[17]
或一小撮桉树叶”,兑着1品脱
[18]
水喝下。复方安息香酊含
有安息香,是一种从几种不同的树皮里提取出来的树脂。我在急诊室一
直使用安息香,我会在包扎伤口前先在伤口周围擦上安息香,这样可以
使包扎更牢固。但是,它对治疗流感没任何作用。
霍普柯克,就像他那个时代的许多医生一样,也用奎宁(quinine)
来治疗流感
[19]。图片来自佛蒙特州报纸数码化项目
“在奎宁中,”他自信地写道,“有一种成分不仅可以控制与发酵有
关的发热进程,而且对流感病毒本身也具有一定的抗毒性作用。”
又是树皮。奎宁提取自南美的金鸡纳树(the cinchona tree)的树
皮。当地人用它来治疗疟疾。到17世纪中叶,它被传入欧洲,以“耶稣
会 士之粉”
[20]
(Jesuits’ powder)的名字(以当时将其带入意大利的宗
教团体的名字命名)为人们所知。直到10年前,奎宁还是治疗疟疾的一
线药物
[21]
,现在它在根除疟疾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么,它又
是怎么被用于治疗流感的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像流感一样,疟疾也会引起发热,而奎宁可以减
少发热频次,能有效缓解症状。如果奎宁可以治愈与疟疾相关的发热,为何不能将其用于治疗所有的发热呢?
[22]
所以,奎宁就成了对抗流感
的“武器库”里的标准化装备。当大流感发生时,奎宁在英国
[23]
、美国[24]
、欧洲大陆
[25]
被广泛使用。“Grove’s Tasteless Chill Tonic”是当时卖
得最好的奎宁产品。作为治疗疟疾的药物,这个产品使爱德文·威利·格
罗夫(Edwin Wiley Grove)在1870年年底一夜暴富。如今,它成为市场
畅销的治疗流感的药物。在全国的各类报纸广告上,这种奎宁水被宣称
可以“使人体系统变得强壮,可以用于治疗感冒、痉挛和流感,改善食
欲、让脸颊恢复红光、重获活力、净化血液,让人变得充满活力”。它
不仅有明显的“强身健体的功效”,而且不会引起胃部不适或者导致“紧
张或耳鸣”
[26]。
但是奎宁并不会像阿司匹林那样直接减少发热,所以它对于流感引
起的发热起不到作用。更糟糕的是,服用高剂量的奎宁
[27]
还会引起视
力问题,甚至导致失明、耳鸣和心律不齐。总之,对于流感而言,奎宁
是一种危险性高且毫无用处的药物。
对于霍普柯克收治的可怜的病人们来说,有毒的汞和树的汁液还不
是全部的治疗药物。对于因流感引起的恶心和呕吐患者,霍普柯克医生
还会给他们服用少量的干香槟(dry champagne)
[28]。
“对于感染了流感的病人而言,没什么比发出滋滋气泡声的香槟酒
更能唤醒他们的了。”
[29]
霍普柯克写道。
如果说这听上去还有点道理,那也只能局限在当时那个时代。即使
在100年前,医疗界也认为霍普柯克的建议是奇怪的。《美国医学 协会
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的一位匿名评论
员难掩蔑视地写道
[30]
:
国外的医生们,尤其是英国的,可能会将这么一本书视作可以接受的或者是富有
建设性的。但是对于广大美国人而言,从普通的教科书中就能获得相同质量的有用信
息,而不会通过持续不断地推荐无效的药物治疗来归纳推理。让我震惊的是,斯克里
布纳出版社(Scribner)居然同意出版这么一本书。确实令人震惊。但是霍普柯克的疗法并非你想象的那样不同寻常。
事实上,这些方法似乎相当主流(即使在美国,这让那个暴脾气的评论
员很是恼怒)。
关于我们如何与流感做斗争的,我最喜欢讲的例子就是1936年一个
流感病人的护理记录。这份记录被当成传家宝保存了下来,并在70年后
出版了
[31]。在3个星期的治疗里,这位病人经历了一连串惩罚性的安慰
剂治疗:芥末石膏粉(一种民间偏方,涂在皮肤上)、阿司匹林(治疗
发烧)、可待因(codeine,治疗咳嗽)、酚酞(phenolphthalein,一种
会致癌的泻药)、其他咳嗽药、樟脑油、7次灌肠(7次!)、直肠管
(别问做什么用)、镁乳(另一种泻药,求上帝快去帮帮他)、乌洛托
品(urotropine,一种尿道抗菌药),以及安息香酊。这个病人至少服用
了5次处方剂量的威士忌和14次蓖麻油。事实上,他的7次灌肠从医学上
讲是必须的,因为他至少服用了39次可待因,虽然抑制了咳嗽,但也会
引起便秘。
当时距离流感大流行已经过去了近20年,但仍然有病人在用修道士
的香脂和蓖麻油进行治疗。我们可以从霍普柯克1914年出版的书里和那
个接受了过度治疗的可怜病人的护理记录里总结出来的是,医生用了许
多民间偏方对付流感,这些偏方往好了说是没用,往坏了说就是有毒。
有些方子至少还是天然有机的:燃烧橘子皮、把洋葱切成丁来熏屋
子(灭菌)
[32]。许多医生 甚至自己配置药液和药物,并基于很难让人
信服的统计数据来推广它们。1919年2月,一位来自芝加哥的伯纳德·马
洛伊(Bernard Maloy)医生宣称,他已经治疗了225名肺炎患者,无1例
死亡
[33]。他使用了两种植物的酊剂——乌头(aconite)和绿藜芦
(veratrum viride),并用了10倍剂量的治疗方案。我们现在已经无从得
知每种成分的浓度,但是乌头(也叫monkshood)和绿藜芦(也叫false
hellebore或Indian poke)都是有毒的植物(如你所料)。一定剂量下,它们会引起恶心、呕吐和血压的断崖式下降,甚至有可能致命。马洛伊
的混合物肯定经过小心地滴定配置,以防出现副作用。我们不能忘记的
是,许多现代药物超过一定剂量也是有毒的。另外,他宣称这种混合物
可以100%预防或者可能阻断肺炎,这意味着,他的病人是被精心挑选
的,那些有着严重的流感或肺炎症状的病例被排除在了他的方案之外。
1918年流感大流行期间,有些人非常绝望,从而铤而走险,在没有
医生的指导下自己发明了充满危险的治疗方法。当流感恶魔在英国西南
部沿海小镇咆哮而过时,法尔茅斯的村民们并没有把他们生病的孩子送
去医院,而是带到了当地的煤气厂去吸煤气。家长们认为让孩子接触有
毒气体可以减轻他们的症状。
A·格雷戈尔上尉(A. Gregor),一位公共卫生官员开始通过观察法
尔茅斯不同人群的流感患病率来确认这种观点
[34]
是否科学。在一个海
军巡逻队基地,他注意到流感患病率为40%。在当地一个驻扎了1000个
连队的陆军军营里,患病率不足20%。在当地一个锡矿场,工人们暴露
于充满硝酸的毒气中,流感感染率只有11%。另外一些锡矿场工人暴露
于炸药和黑火药中,这些吸入毒气的“幸运儿”的流感感染率更低,只有
5%。
许多“脑子里的感冒”可以用烟气来治愈是一种流行的观点,这个观
点有“一定的事实基础”。格雷戈尔在1919年的《英国医学杂志》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上总结道。此时,流感大流行正在逐渐减
弱。他不是唯一一个持这种观点的人。另外一名医生的报告指出:“有
充分证据说明,毒气厂的工人们
[35]
实际上对流感有免疫力。”令人感到
欣慰的是,没人真的建议通过吸毒气来预防流感,即使是那个很喜欢升
汞的霍普柯克医生也没这么做。
格雷戈尔的发现是否真的和工人们暴露于毒气之中有关,现在已经
无从知晓。氯气确实可以杀死禽流感病毒,也有可能会杀灭煤气厂工人们身边飘浮着的流感病毒
[36]。但我们需要记住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期间,氯气以最残忍的方式杀死了许许多多的士兵。
————
并非所有医生都会像流感大流行期间的江湖郎中那样去给病人看
病。詹姆斯·亨里克(James Herrick)是一名在芝加哥工作的医生,曾就
读于伊利诺伊的拉什医学院(Rush Medical College),被公认为是一位
成功的医生
[37]。1910年,他是第一个描述后来被称为镰刀形红细胞贫
血症的人,尽管在当时,他还无法解释这种疾病的病因。两年后,他发
表了一篇关于冠状动脉疾病的重要综述,他认为这些动脉可能被堵塞,但不会马上致死。这和当时盛行的观点截然不同。基于经验,他成功地
描述了这些堵塞所引发的临床症状,比心血管造影技术出现整整早了1
个世纪。他的这些研究成果奠定了现代心脏病学的基础
[38]。此外,他
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肺炎、白血病和包括流感在内的其他疾病的文章。
亨里克是最早向神水和民间偏方发起 挑战的人之一,这些东西确
实让流感病人受到了伤害,甚至因此而丧命。亨里克经历了两次流感大
流行,分别是1890年和1918年。他的诉求很简单
[39]
:在没有证据表明
它们会起作用之前,医生们不能把能用的药都用上。
在1919年夏天写下这篇文章需要很大的勇气,当时美国和世界其他
地区正从史上最严重的流感大流行中恢复过来。亨里克写道,“大多数
治疗流感的医生都是基于‘肤浅的观察和有限的经验’而进行治疗的。他
们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疾病是有自限性的,即它常常能够自愈。”
“所以许多结论都是很粗糙的,”亨里克写道,“它们是通过臆想得
出的,在这个过程中,乐观的轻信取代了探索性的科学质疑。”
亨里克对各种粗制滥造的治疗方案持怀疑态度,这些疗法轻则会让病人神志不清,重则会致死。打一针水银?超高剂量的奎宁?“当
然,”他用一种特有的轻描淡写的语气写道,“有的人得出这些结论时犯
了错误。”
[40]
亨里克说:“让我们尝试一些更切合实际的真正有效的方法,而不
是开些毫无作用的药物。例如,隔离和戴口罩,以防止传染;让病人多
喝水,以防止脱水;还要多休息,要好好地休息。”几周的卧床休息,少量户外活动,多呼吸新鲜空气,保持安静,多睡觉。他的治疗方案恰
恰代表了保守派的主流意见
[41]。
当然,亨里克也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所以我们也不必惊讶于他也
赞成使用泻药
[42]
,并坚持“在患病初期肠道必须彻底打开,且在任何时
候都不可以让肠道失去活力”。我们应该对他的这个观点表示宽容和理
解,因为他发表了一些其他超越时代局限的常识性观点:
在治疗严重的自限性传染病时,最难做到的事情之一就是不要仅仅因为确诊了就
开药。当想到流感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时,头脑再冷静的医生的自我约束也会被置之
脑后。在流感肆虐的时候,带着一丝歇斯底里的恐慌气氛在人群中蔓延扩散,医生过
去形成的良好判断力也会变得找不着方向。医生会忘记其实大多数流感病人根本不需
要服用什么药物。本来就不该有什么常规治疗方案规定了某些药物应该在某个时间段
使用,而根本不考虑是否有一个清晰的用药指征。治疗方案应该给患者带来希望,根
据患者的症状来确定,因人而异。
最后一句是金句。这句话值得每所医学院的每位医学生牢记。等一
等,看一看会发生什么,针对病人的症状用药,看看病人的个人档案,考虑病人的情况,进行个性化治疗。
幸运的是,也有其他一些医生认为大多数的流感治疗都是不正确
的。1918年11月,一名驻扎在英格兰布兰肖特营地的加拿大随军医生写
道,对于大量用于流感治疗的药物而言
[43]
,“显而易见,它们大部分都
是徒劳无功的”。几千年以来的治疗方法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但从某种程度上说,病人并没有变化。毕竟病毒的类型是一样的,折磨
古希腊人的病毒,也是把不幸的灵魂送到霍普柯克医生面前的病毒,也
是把你的配偶、孩子或你自己打倒的病毒。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
当然,我的同事们至少不会给你开一剂泻药。我也不会让你去放
血。但当你得知这么多年来流感的治疗方案并没有多大的进步时,你或
许会感到惊讶。
下面是美国每年会发生3100万次以上的事件的 一个典型总结
[44]。
深秋时节的某个周五的晚上,你开始觉得不舒服。你感到疲惫,不想吃
东西。你的后背和大腿开始疼痛。然后你觉得一阵寒战,开始冒汗。你
量了下体温,102华氏度(约39摄氏度)。现在你真正开始感到难受
了。寒战变得更厉害了。你的喉咙开始觉得痒痒,继而是疼痛。你开始
打喷嚏。到了周六的早上,你开始流鼻涕、咳嗽,而且觉得全身酸疼。
你得了流感。
对于这一常见的场景,每个人的反应都有所不同。你可能会待在家
里,服用泰诺或布洛芬,把体温降下来,并缓解疼痛。你也可能躺在床
上,睡睡醒醒。如果你是个幸运儿,或许会有人来照顾你,给你端来一
杯热水或热饮料。过了两天,你终于不再发烧,体力也开始恢复。到了
周一,你只好请病假,但你终于可以拖着沉重的身子去浴室洗澡了。尽
管没有食欲,但你可以喝点汤。到了周二,烧退了,你的食欲也在慢慢
恢复。到了周三,你已经痊愈了,可以重回办公室了。
这是大多数健康人得了流感之后的表现。只是大多数,不是全部。
有些人在开始有发烧或身体疼痛的迹象时,会联系他们的初级保健医
生。医生会告诉他们待在家里多喝水,如果症状没有好转就去急救中心。到他的诊室去,是医生最后才会想让你做的事。这样你就会把病毒
传染给他、他的员工和其他的病人。我在急救中心诊治过数以百计的流
感病人,许多人还处在发病早期,甚至有些人的症状还不明显,而我能
做的就是让他们回家,并送上我妈妈常对我说的嘱咐:多喝鸡汤。
不过有些病人得了流感却会有生命危险。他们可能是老年人,或是
免疫系统受到艾滋病病毒、化疗、或甾体类药物损害的人。还有些人可
能免疫系统是健全的,但是不巧遇上了某种特定流感的大暴发。还有的
人可能平时饮水不足,或者是由于呕吐或腹泻导致脱水。这些都是流感
的重症病例,常常需要到急救中心来救治。他们大多数是开车或坐出租
车来的,还有些是救护车送来的。
不管是以何种方式来的,到了急救中心后 遇到的第一个人肯定是
分诊护士。她会快速询问病人的病史,然后测量他们的脉搏、血压和体
温,并把一根探头放在他们的指头上来检测血液中的氧气含量(血气
针)。如果这四项检测(汇总起来就是你的“生命指征”)高于或低于正
常值,就会被要求戴上口罩,坐在等候室,直到有空的床位。坐在那里
时可能会看到其他三三两两戴着口罩的病人,穿着睡衣,肩上披着宽大
衣服,也在候诊。已经虚弱到无法走路的病人会被优先安排进入急救中
心。
如果是特别严重的流感季,会有许多症状一样的病人挤满了等候
室。如果是在下午或傍晚到达,那是大多数急救中心的高峰时段,候诊
时间会相对较长。如果在城里的急救中心就诊,那么会比在郊区的急救
中心就诊花费更长的候诊时间。周五和周一常常是一周里最忙的时候,而联邦假期和清晨的几个小时常常是人最少的时段
[45]。联邦假期后的
第一天,急救中心常常极其忙碌。请记住,医务人员在换班时可能动作
最为缓慢
[46]。我把上述信息都放在一起,是为了告诉你,如果得了严
重的流感,需要去看急诊,那么最好是在圣诞节假期的早上7点。一旦有了床位,病人会被扎很多针,其中一根静脉针刺入血管,取
血样。这些都是在医生看 到病人之前完成的。当医生来了以后,他会
问病况:起始时间、症状,等等。医生这样问有两个目的:第一,排除
病人没有肺炎等需要注射抗生素或住院的严重疾病;第二,想要弄清楚
是否需要其他的干预措施,比如额外的静脉输液。如果病人确实患了流
感,而且不需要静脉输液,那么只需要一些泰诺(在美国是一笔相当昂
贵的医药费账单)就可以回家了。
那么,医生是如何知道病人是否感染了流感呢?我不得不承认,即
使经历了5年的医学院教育、4年的住院医师培训和几千个小时的看诊,我们在急救中心的大多数医生也只是凭直觉判断。当然我们会问些重要
的问题来排除某些疾病,比如“你近期去过非洲吗?”或者“你是否曾接
触过一氧化碳?”最后一个问题很重要。如果病人没有因为一氧化碳中
毒身亡,那么一氧化碳会引起酷似流感的症状。流感高发期是在秋冬两
季——此时人们会用加热器和火炉,一氧化碳中毒常常被误诊为流感。
几年前,一起医疗事故索赔诉讼中,我作为专家见证人出庭作证。
在这个案子里,丈夫、妻子和儿子被发现死于他们费城的家中,死因是
一氧化碳中毒。后来发现,这位妻子曾去当地的急救中心就诊,症状是
头痛、恶心和呕吐。她去了两次。但是医生两次都没有考虑到一氧化碳
中毒的可能,相反,她的症状被认为是流感引起的。陪审团最后裁定被
告支付近190万美元赔偿款
[47]。
一旦确诊为流感,医生们就开始讨论治疗方法。如果有发烧,医生
会建议服用退烧药。这是每个急诊科医生都会做的事,也包括我。但事
实上,我们最好问问是否真的应该把烧退下来。
对于几乎所有人而言,发热从任何角度考虑都 不是危险的。但它
们让人难受,所以我们要去对付它们
[48]。有证据表明,发热其实是有
益的。原因很简单:当身体发热时,免疫系统能够更好地抵抗感染。当白细胞大量从骨髓中释放出来时,它们能够更好地和感染作战。发热还
可以增强另外一群叫自然杀伤细胞(NK细胞)的血细胞的活力
[49]
,提
升巨噬细胞(macrophages,希腊语里是“大胃王”的意思)吞噬和摧毁入
侵细胞的能力。
当体温略微升高时,身体能够更好地与感染做斗争,那么如果退烧
之后是否会给病人带来更糟糕的后果呢?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一个
研究小组对一组人进行了观察,他们想看看那些服用了退烧药物的流感
病人会发生什么。一旦他们觉得身体好些了,流感病人们就会下床,参
加社交,同时也开始传播病毒。从整个人口层面看,影响相当大。麦克
马斯特小组认为,频繁用药物干预发热的操作会将流感的传播性增强至
少1%。我知道这听起来也没什么,但是可别忘了美国每年死于流感的
人数高达4.9万
[50]。如果你把麦克马斯特小组的预估代入这些流感数字
中
[51]
,美国每年差不多有500人(或许其他地方有更多人)可以通过在
流感治疗中避免使用退烧药而被救回来。
在急救中心,我也总是会给发热的流感病人开药。而且,据我所
知,每个急诊科医生都会这么做。一部分原因是我接受过职业培训,另
一部分原因是发热真的让人难受。同时,这也是病人所希望的。人们希
望发热能够被治疗。此时向一个渴望浑身疼痛得到缓解的病人去解释麦
克马斯特的研究论文就显得费时费力了。
我常常给流感病人提供的另一种 治疗方法是静脉输液。对于有脱
水症状的病人,这非常重要。经过一两袋含有无菌水、盐和一些电解质
的静脉输液后,病人常常感到明显好转。我见过无数流感病人被救护车
送到急救中心,虚弱到无法站立。1小时后,输了两袋流体,他们就能
够走出急救中心自行回家了
[52]。
验血通常不是必要的,胸部X光检查也只会让病人受到不必要的辐
射。有的病人可能来到急救中心时流感症状没那么重,却希望医生能够给他做血液和X射线检测。事实上,没有必要将这些检查视作一理所当
然的常规操作。把这个决定权交给医生,不要自己主动提出来要做血检
或X射线。这些检查除了增加你账单上的数字,毫无用处。我几乎从不
开这类检查,但也有例外。一些病人看起来非常虚弱,极度脱水,或者
合并其他慢性病。还有些人可能是老烟鬼,还有些人可能已经得了肺
炎。他们可能会窒息。当我借助于听诊器听他们的肺音时,能听到噼啪
声和喘气声(或者叫“罗音”[rales]和“干罗音”[rhonchi])。对这些
病人来说,肺部X光片是必须要做的,因为通过片子可以判断是否得了
肺炎。血液检测将会发现有大量的白细胞,提示有一系列感染。我能够
给予这些病人的首要治疗步骤就是让他们吸纯氧。在我们的肺里有成千
上万个小囊泡,叫肺泡,氧气通过肺泡进入我们的血流。在被流感和肺
炎破坏的肺中,这些肺泡充溢着体液和脓液,进入血液的氧气有所减
少,导致呼吸短促急迫。含氧量高的血液颜色是鲜红的,没有氧气的血
液颜色是暗红的。当氧气水平变得相当低时,嘴唇和耳朵会变得暗沉。
这被称为紫绀,是病人病情严重的信号。这也是1918年流感大流行时重
症病例的共同特点之一。吸氧可以用来治疗紫绀或低血氧症,并在几分
钟之内就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
这些病重的患者必须住院,接受抗生素治疗以对抗肺部的细菌感
染。他们还需要输液,以保持他们身体水分充足,需要继续保持吸纯
氧。大多数人只需要在病房里待几天病情就可以改善,但如果肺部受损
严重、扩散范围持续扩大,就需要转移到重症监护病房。在那里,每个
病人都有专门的护士看护,病情的每个变化都需要密切监视。如果病情
恶化,需要使用镇静剂,同时连接上一个可以代替他们呼吸的机器。一
根大约9英寸长、食指粗细的管子通过喉咙沿着气管滑进去。一端连着
呼吸机,每循环一次,病人的胸部就会扩张收缩一次。然后我们能做的
就是等待了。
如果一切顺利,肺炎会缓解,流感引起的炎症也会慢慢消退。几天后就可以撤去呼吸管,镇静剂的用量也会慢慢减少。病人慢慢苏醒,对
刚刚进行的激烈的生死之战一无所知。这是一切顺利的结果。但有时候
肺炎太严重以至于病情无法得到有效控制。首先肺功能会衰竭,然后是
肾和肝等多个器官衰竭。最后,流感又将夺去一个生命。
我这么说并非出于一种病态。在每年感染流感的数百万人中,只有
不到1%的人会死亡。对于来到急救中心的人来说,大多数人只是需要
被医生再次告知“时间”是治愈流感所需要的一切。现在最大的误区之一
是不管大小病都需要抗生素。如果一个健康人得了普通流感,不需要抗
生素,医生也不该开抗生素类的药物。抗生素对病毒没用,所以它们对
治疗流感也一点儿用都没有。然而如果有并发症且病毒性流感发展成了
细菌性肺炎,此时当然应该用抗生素。但是,我要重复一遍的是,抗生
素对流感病毒没用。你也许会惊讶,竟然有这么多的患者明知是病毒感
染还是会要求医生开抗生素。当我拒绝了他们的要求时,他们会失望不
满。医生需要对这个问题负主要责任。有可信的数据显示,有大约一半
病毒感染患者(如“流感”)拿到了完全没用的抗生素
[53]。
简直无法想象,我们曾经将放血、灌肠、香槟、毒气、蓖麻油视作
治疗流感最先进的方法。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我们经历了漫长的探索。尽
管现代医学显示出了种种优越性,但治愈流感仍然是我们未解决的难
题。我们仍然受到流感病毒的威胁,担心1918年流感大流行会卷土重
来。要想知道为什么流感依然难以治愈,我们需要深入了解病毒本身。
[1] K. Saketkhoo,A. Januszkiewicz,and M. A.Sackner,“Effects of Drinking Hot Water,Cold Water,and Chicken Soup on Nasal Mucus Velocity and Nasal Airflow Resistance”,Chest 74,no.4 (1978):408-10.
[2] B. O. Rennard et al.,“Chicken Soup Inhibits Neutrophil Chemotaxis In Vitro”,Chest 118
no.4 (2000):1150-57.
[3] “Chicken Soup for a Cold”.2017年12月10日登录,https:www.unmc.edupublicrelationsmediapress-kitschicken-soup.[4] D. M. Morens,“Death of a President”,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41,no.24
(1999):1845-49.
[5] Mary Thompson,“Death Defied”,George Washington’s Mount Vernon.2017年11月11日登
录,http:www.mountvernon.orggeorge-washingtonthe-man-the-mythdeath-defied-dr-thorntons-
radical-idea-of-bringing-george-washingtonback-to-life.
[6] 盖伦,即克劳迪亚斯·盖伦(Claudius Galenus,129-199),是古罗马时期颇具影响力的
著名医学大师,他被认为是仅次于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医学权威。盖伦是著名的医
生、动物解剖学家和哲学家。他一生专心致力于医疗实践解剖研究、写作和各类学术活动,撰
写了五百多部医学著作,并根据古希腊体液说提出了人格类型的概念,主要作品有《气质》
《本能》《关于自然科学的三篇论文》。——译者注
[7] J. A. B. Hammond,W. Rolland,and T. H. G. Shore,“PurulentBronchitis:A Study of
Cases Occurring amongst the British Troops ata Base in France”,Lancet 190,no.4898 (1917):
41-45.
[8] C. E. Cooper Cole,“Preliminary Report on InfluenzaEpidemic at Bramshott in September-
October,1918”,British Medical Journal 2,no.3021 (1918):566-68. “In some cases
venesection relievedthe toxemia,especially if ombined with (1)saline or (2)glucose and
salineinterstitially,intravenously,or by the rectum.”
[9] Heinrich Stern,Theory and Practice of Bloodletting (NewYork:Rebman Company,1915),iv.
[10] W. F. Petersen and S. A. Levinson,“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Venesection with Reference
to Lobar Pneumonia”,JAMA 78,no.4 (1922):257-58. 彼得森(Petersen)和列文森
(Levinson)是真正支持放血疗法的人。“我们相信放血疗法,并想向许多年长的有能力的临床
医生强调,静脉放血术有时可带来显著的疗效,这种疗效具有明确且合理的基础。”
[11] 但是这仍然经历了较长时间。在G.B.Risse的文章里,作者讨论了它是如何退出历史舞
台的:“The Renaissance of Bloodletting:A Chapter in Modern Therapeutics”,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and Allied Sciences 34,no.1 (1979):3-22.
[12] A. F. Hopkirk,Influenza:Its History,Nature,Cause and Treatment (New York:The
Walter Scott Publishing Company,1914),155. 在这里我可能太苛刻了,因为几乎所有医生在
治病时(不管是何种临床症状)都会用同样的方法,即泻药和催吐药。见David Wootton,Bad
Medicine:Doctors Doing Harm Since Hippocrate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13] 1917年2月,阿司匹林生产厂商拜耳失去了该药物的专利,其他生产企业可以生产该药
物并涌入市场,使得人们在不管是何种治疗方案下都能够很容易获得大剂量的阿司匹林。1918
年9月,美国卫生局局长表示,阿司匹林已经在国外成功用于缓解各类疾病症状。在随后的一个月内,流感死亡人数达到峰值。
[14] Richard Collier,The Plague of the Spanish Lady:The Influenza Pandemic of 1918-1919
(London:Macmillan,1974),106.
[15] 格令,是历史上使用过的一种重量单位,1格令等于0.0648克,一般用于称量药物等。
——译者注
[16] 参见K. M. Starko,“Salicylates and Pandemic Influenza Mortality,1918-1919
Pharmacology,Pathology,and Historic Evidence”,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 49,no.9
(2009):1405-10. 另参见JohnM. Barry,The Great Influenza:The Epic Story of the Deadliest
Plague in History (New York:Penguin,2005),353,358.
[17] Hopkirk,Influenza ,159.
[18] 品脱,容量单位,英制1品脱等于0.5683升。——译者注
[19] Hopkrik,Influenza ,156.
[20] D. C. Smith,“Quinine and Fever:The Development of the Effective Dosage”,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s 31,no.3 (1976):343-67.
[2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Guidelines for the Treatment of Malaria”,Geneva,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15.
[22] Smith,“Quinine and Fever.”
[23] Cooper Cole,“Preliminary Report on Influenza Epidemic at Bramshott.”
[24] H. A. Klein,“The Treatment of ‘Spanish Influenza’”,JAMA 71,no.18 (1918):1510.
[25] “...iletaitlogique d’avoirrecours aux injectionspour traitercette infection comme on le fait pour
le paludisme.”参见F. Fabier,“Traitement de la Grippe par les Injections de Quinine”,Journal de
Médecine et de Chirurgie Pratiques 90 (1919):783-84,另参见M. L.Hildreth,“The Influenza
Epidemic of 1918-1919 in France:Contemporary Concepts of Aetiology,Therapy,and
Prevention,”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4,no.2 (1991):277-94 .
[26] 参见Muskogee Times-Democrat ,December 1,1919,6.
[27] M. E. Boland,S. M. Roper,and J. A. Henry,“Complications of Quinine
Poisoning”,Lancet 1,no.8425 (1985):384-85.
[28] Hopkirk,Influenza ,163,180.[29] Hopkirk,Influenza ,167.
[30] “Influenza:Its History,Nature,Cause and Treatment”,book review,JAMA 63,no.3
(1914):267.我仍然无法确信评论员蔑视的是谁,英国人还是霍普柯克医生?我喜欢“万灵
药”(nostrum)这个词,它意味着一种由不合格的人制备的无效的药物。
[31] R. J. Sherertz and H. J. Sherertz,“Influenza in the Preantibiotic Era”,Infectious Diseases in
Clinical Practice 14,no.3 (2006):127.
[32] Roger Welsch,A Treasury of Nebraska Pioneer Folklore (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67),370.
[33] “Influenza Discussions”,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no.2 (1919):136.
[34] A. Gregor,“A Note on the Epidemiology of Influenza among Workers”,British Medical
Journal 1,no.3035 (1919):242-43.
[35] F. Shufflebotham,“Influenza among Poison Gas Workers”,British Medical Journal 1,no.3042 (1919):478-79. 由于某些原因,这种免疫并未延展到光子气工人身上。光子气在第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产生了非常恐怖的效果。
[36] E. W. Rice et al.,“Chlorine Inactivationof Highly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 Virus
(H5N1)”,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13,no.10 (2007):1568-70.
[37] “James B. Herrick (1861-1954)”,JAMA 16,no.186(1963):722-23.
[38] 参见C. S. Roberts,“Herrick and Heart Disease”,in H. Kenneth Walker,W. Dallas Hall,and J. Willis Hurst,eds.,Clinical Methods:The History,Physical,and Laboratory Examinations
,3rd ed. (Atlanta:Butterworth Publishers,1990). 另参见R. S. Ross,“A Parlous State of Storm
and Stress. The Life and Times of James B. Herrick”,Circulation 67,no.5 (1983):955-59.
[39] James B. Herrick,“Treatment of Influenza by Means Other Than Vaccines and
Serums”,JAMA 73,no. 7 (1919):482-87.
[40] 所有这些引言都是来自亨里克,483.
[41] “Proceedings of the Forty-Six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no.2 (1919):130-42.
[42] 这段引言来自亨里克,483. 这种对流感病人的肠蠕动的关注获得了非常广泛的传播,并成为医学根深蒂固的知识。这里是一封医生的信件的节选,于1918年11月发表在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我不能过于强调使用温和的泻药使肠道畅通的重要性,但常
见的情况是,在肠道的一次快速导泻之后,高烧会缓慢消退,这种方法对于缩短流感的病程非常有帮助。”来自Klein,“The Treatment of ‘Spanish Influenza’”,1510.
[43] Cooper Cole,“Preliminary Report on Influenza Epidemic at Bramshott”.
[44] N. A. Molinari et al.,“The AnnualI mpact of Seasonal Influenza in the U.S.:Measuring
Disease Burden and Costs”,Vaccine 25,no.27 (2007):5086-96.
[45] 这些观察是基于我自己25年来在美国和国外多个急救中心的工作经历。幸运的是,我
的经历似乎和已发表的数据高度匹配。我的前同事梅丽莎·麦卡锡(Melissa McCarthy)对一个
大型的市区教学医院急救中心接收病人的时间点持续了超过一年的研究。她发现,周一和周五
最忙,并且早上较早的几个小时是最悠闲的。See M. L.McCarthy et al.,“The Challenge of
Predicting Demand for Emergency Department Services”,Academic Emergency Medicine 15,no.4
(2008):337-46.另见S. J. Welch,S. S. Jones,and T. Allen,“Mapping the 24-Hour Emergency
Department Cycle to Improve Patient Flow”,Joint Commission Journalon Quality and Patient Safety
33,no.5 (2007):247-55. 这些模式在全世界的急救机构中都有被发现,如Y. Tiwari,S.
Goel,A. Singh,“Arrival Time Pattern and Waiting Time Distribution of Patients in the Emergency
Outpatient Department of a Tertiary Level Health Care Institution of North India”,Journal of
Emergencies,Trauma,and Shock 7,no.3 (2014):160-65.
[46] 大多数急救室是三班倒:早上7点到下午3点、下午3点到晚上11点、晚上11点到第二天
7点。此外,对于一家特定的急救室而言,会有许多额外的班次的重叠组合,这取决于病人达到
高峰的时间。
[47] A. Elliott-Engel,“Jury Awards 1.87 Million in CarbonMonoxide Poisoning Case”,Legal
Intelligencer ,June 1,2011.
[48] 参见M. Glatstein and D. Scolnik,“Fever:To Treat or Not to Treat?” World Journal of
Pediatrics 4,no.4 (2008):245-47. Adated but useful review of the subject is Matthew J. Kluger,Fever:Its Biology,Evolution,and Function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
[49] 有一项关于发烧和免疫热调节的综述写道:“发烧所带来的体温升高是一种全身报警系
统,它可以在外来病原体入侵时广泛地激发免疫监视。”参见 S. S. Evans,E. A. Repasky,and
D. T. Fisher,“Fever and the Thermal Regulation of Immunity:The Immune System Feels the
Heat”,National Review of Immunology 15,no.6 (2015):335-49.
[50] 这是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估计,参见“Estimating Seasonal Influenza-Related
Deaths in the United States”.
[51] D. J. Earn,P. W. Andrews,and B. M. Bolker,“Population-Level Effects of Suppressing
Fever”,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Biological Sciences 281,no.1778 (2014):
20132570.[52] 静脉输液是一种简单的介入治疗方式。生产厂家对一袋输液的定价只有1美元,但是医
院往往会有较高的加成。《纽约时报》有个调查显示,有些人被要价787美元用于支付“输液治
疗”。还有一个例子,一个病人被要求花费91美元来支付一个医院采购成本仅有0.86美元的输
液。你可以把酒店的迷你吧当成某种意义上的敲诈。参见Nina Bernstein,“How to Charge 546
for Six Liters of Saltwater”,New York Times ,August 27,2013.
[53] C. G. Grijalva,J. P. Nuorti,and M. R. Griffin,“Antibiotic Prescription Rates for Acute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s in U.S. Ambulatory Settings”,JAMA 302,no. 7 (2009):758-66.2 流感:病毒的前世今生
病毒早在人类诞生之前就已存在。病毒诞生的时间比智慧生命、类
人猿、黑猩猩、爬行动物以及任何从黏液中孕育的生命诞生的时间都要
久远。病毒无处不在,天生神秘。我们并不知道病毒是如何演变发展
的,但我们知道它们已经存在了数百万年。病毒存在于生命的边缘
[1]
,挑战我们对生物的认知。石头没有生命,但是细菌有,病毒则介于两者
之间。
病毒是一系列不具备基本细胞结构的化学物质组成的盒子。病毒不
能自行代谢或再生。为了繁殖,它必须入侵活体细胞。病毒能够感染细
菌、植物、爬行动物、鱼类、鸟类以及哺乳动物。病毒与人类的进化密
不可分。几千年来,部分病毒已与人类的遗传密码合为一体
[2]。隐蔽于
人类DNA长链中的序列就源自古代的病毒。他们的遗传密码与我们的遗
传密码息息相关,病毒由此成为人体无害的一部分。病毒的繁衍完全依
靠人体细胞来获取营养。
————
“virus”(病毒)一词在人类发现病毒颗粒 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这是
一个拉丁词语
[3]
,意思是“毒药”“毒液”或“有害气味”。中世纪,“病
毒”与“毒素”同义。在拉丁文医学文本的英文版本中,这个词仍未经过
翻译。到了18世纪,病毒一词可以用来指代任何传染病。例如,爱德华
·詹纳(Edward Jenner)
[4]
在发现预防天花的疫苗之前,就用这个词来
描述天花产生的原因。在19世纪,伴随着疾病细菌理论的迅速发展,“病毒”一词依然被用来表示致病因子,或有无细菌感染。路易·帕
斯特(Louis Pasteur)将引起狂犬病的致病因子称之为“levirus rabique”
[5]。如今,我们知道病毒属于亚微观实体,其体积比细菌还要小20倍。病
毒的核心部分是遗传物质
[6]
,外面覆盖着蛋白质外壳,它们仅能在活体
细胞内繁殖。
正如“病毒”一词在具备如今的意义之前就已经被人们使用了很久一
样,“流感”一词诞生的时间也比目前人们使用的时间要久远。没有人能
够确定英文词语“influenza”最初是否用来描述目前被人们称之为“流
感”的这种疾病,但早在1504年,这个词语就出现了。该词来自意大利
语,意思是“影响”(influence)。这就说明它源自占星理论。人类曾经
认为流感是由恒星和行星的错位造成的。
直到20世纪,我们才确切地知道病毒到底是什么。在此之前的数千
年间,人类一直为这种看不见的力量所困扰,并为此做了种种假设。撰
写了爆发于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古希腊历史学家修
昔底德(Thucydides),记录了公元前430年发生的一场长达3年的瘟疫
[7]。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雅典寻求庇护。这座城市很快就人满为患。这
就为传染病的暴发创造了最佳条件。修昔底德描述这种疾病最初的症状
是“头部发热和眼睛发红”,之后出现打喷嚏以及声音嘶哑症状,“不久
后,这些症状演变为胸腔剧烈的 咳嗽”。高烧严重时,患者们不得不跳
入蓄水池为自己降温,而且他们还会通过喝酒来缓解持续的口渴。修昔
底德对患者的存活时间感到诧异,然而,大多患者在一周内就殒命了。
驻扎在雅典的1.3万名士兵中有三分之一的人被这场流行病夺去了生
命。然后,奇怪的是,在公元前427年的冬天,这场流行病出乎意料地
结束了。
长期以来,这种疾病一直被视为历史谜团。有人怀疑是瘟疫和斑疹
伤寒,但也有人说是炭疽、伤寒和肺结核。这种疾病发病快、潜伏期短。那些生病之后得以康复的人——包括修昔底德本人——并没有再患
这种病。这种疾病一波接一波来袭,常见于人口聚集的地方。20世纪80
年代,研究人员将这组病症称为“修昔底德综合征”。研究人员还注意
到,这种疾病的症状具有流感大流行的特征,同时伴有继发细菌性感
染。疾病的暴发与1918年的流感疫情有诸多共同特征,包括造成多人死
亡的继发感染。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修昔底德综合征就是有关流感
的最早记录。由于死亡率极高,所以这种流感也极具致命性。
在修昔底德之后的100年里,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描写了一种听起
来像流感的疾病
[8]
,这种疾病每年暴发一次。这种疾病的外观与在北半
球的秋冬季可见的昴宿星团(the Pleiades,又称“七姐妹星团”)相似。
在这段时间里,希波克拉底写道,“许多人持续不断地发烧”,病人发
冷,经常出汗,并伴有咳嗽。
之后,直至中世纪晚期才有流感暴发的相关记录,此时天花和鼠疫
是最令人恐惧的致命疾病。与这些大规模致命疾病相比,流感的影响力
几乎难以察觉。
几个世纪后的1675年11月,我的家乡伦敦暴 发了一场流感
[9]。每
周的死亡人数从月初的42人增加到月中的130人,而在12月的第一周只
有7人死亡。除了致人死亡之外,这种疾病还有其他麻烦的特征。教堂
里的教徒们咳嗽得太厉害,以至于听不到牧师布道
[10]。有点讽刺意味
的是,英格兰北部的人们称这种疾病是“快乐的咆哮”(jolly rant,现在
该词专指流感患者),因为它将受害者变成了悲惨的噪声制造者。当
然,这并不是什么令人快乐的事。17世纪英国著名的医生托马斯·西德
纳姆(Thomas Sydenham)认为
[11]
,这些流行病与暴雨有关,是暴雨使
人们的血液中布满了“粗糙的含水颗粒”。放血疗法和泻药
[12]
被认为是
最佳的治疗方法。
————为了区分一般流行病和大流行性疾病,我们暂且不讨论血液和排便
这类话题。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些词语都在交替地用来描述流感的
暴发。2009年暴发的流感被称为猪流感。这恰恰是混淆两个术语的典型
例子。《纽约时报》上的一则标题就是“这是大流行性疾病吗?对‘大流
行性疾病’的定义”
[13]。虽然两者的范围和强度有区别,但没有人真正
认可它们的确切含义。我们目前最常用的定义是
[14]
一般流行病是一种
在地方暴发的严重疾病,而大流行性疾病是一种在全球暴发、从源头快
速传播的致人重病的疾病。按这个标准来看,17~19世纪中,每个世纪
都分别出现了3~5次流感大流行。其间一些流感大流行
[15]
暴发的时间
间隔达半个世纪,而其他几次则在几年时间内相继暴发。流感如此令人
困惑的部分原因是:从一般流行病和大流行性疾病的角度来看,随着季
节的更替,小规模的这种疾病可以预测,但是大规模的则无法预测。例
如,1730年的流感后的第二年又暴发了一次流感。在几乎一个世纪之后
的1831年和1833年又连续暴 发了两次流感。流感活动规律如此深不可
测,因此需要很长时间去跟踪和识别。
暴发于19世纪的一场特殊的大流行性疾病与以往的不同,它使人类
在揭开这种疾病的神秘面纱方面向前迈进了一步。1889年冬季暴发的具
有毁灭性的疾病不仅是现代第一次流感大流行,而且也是第一次有且详
细记录在案的流感大流行。据此,人们可以对其传播和影响情况进行评
估。这是40多年来英国暴发的第一次流感大流行。鉴于这场疾病形势严
峻,一位名叫亨利·帕森斯(Henry Parsons)的医生将该病上报给了议会
[16]。帕森斯指出,这次暴发的疾病肯定是一场大流行性疾病,因为整
个欧洲都在饱受病痛的折磨。之后,这种疾病又传播到美国
[17]。1889
年12月,在纽约报告了首起病例。次年1月,波士顿、圣路易斯和新奥
尔良都有人染病死亡。在波士顿,40%的人患病。超过四分之一的工人
因为病情过于严重而无法工作。过度拥挤和致命的“污浊空气”对疾病传
播有巨大的影响。在这场大流行性疾病中,富人和穷人都深受影响,但
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人群密集或密闭场所,患病率会更高”。帕森斯不知所措。他无法提供预防流感的方法,因为还有一个重要
谜团没有解开:病因。这是人们的猜测。帕森斯向议会提交的报告表
明,大流行性疾病已经在俄罗斯暴发,正在向西蔓延。但这里含有多少
科学分析的成分,又有多少具有沙文主义的成分?甚至有传言说
[18]
,这种大流行性疾病是由从俄罗斯进口的燕麦传播到英国的。这些燕麦先
是被马吃掉,然后马将疾病传给了人。其他起源论包括腐烂的动物尸
体、地震、火山爆发以及从“地球的内部最深处”排放到空气中的“臭
气”。甚至有人认为大流行性疾病是由木星和土星共同引起的
[19]。
帕森斯提出了1889年流感大流行暴发的三个可能原因
[20]。第一个
原因是天气。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么多的病 例几乎同时出现在整个
欧洲和美国。可能的原因是空气质量很差。或许大气中携带一种能在空
中繁殖然后感染一些易感人群的有毒物质?帕森斯承认,他知道没有任
何药剂能够做到这一点。尽管他认为这可能是由“非生命的颗粒物”
[21]
引起的——这种对病毒实质的描述非常准确。
第二个原因是流感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家庭
成员之间经常互相感染,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很多情况下某个家庭成
员将疾病传染给了整个家庭。帕森斯获得了英国大型铁路系统工人的流
感数据。感染率较高的是职员
[22]
,尽管他们没有暴露在外面的空气
中,但是每天与许多人接触,而机车驾驶员感染率较低,他们基本上暴
露在公开场合,但与乘客是隔离开的。帕森斯确信
[23]
,人群接触是疾
病传播的罪魁祸首。
帕森斯的第三个原因是,在某种程度上,动物对疾病的传播也起了
一定的作用
[24]
——特别是马、宠物狗、猫和笼养鸟。帕森斯再一次得
出了正确的结论,这一点比其他人早了大约50年。
————在弄清楚什么是病毒之前,科学家已经对细菌有所了解。19世纪40
年代,几位欧洲科学家各自得出结论:发酵过程中必需的酵母菌是一种
生物活体。发酵过程不仅是一种化学过程,也是一种由微生物活动引起
的生物过程。法国人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研究了发酵依赖酵母
和其他肉眼无法看到的微生物的方式。“巴氏杀菌法”就以他的姓氏来命
名加热液体杀死细菌的过程。巴斯德出生于1822年,在将注意力转移到
法国北部边境里尔市(Lille)当地啤酒厂所面临的问题之前,他的研究
领域是化学。他表示,发酵不仅需要活酵母菌,还需要一种微生物,那
就是他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的细菌。
巴斯德的细菌发现从总体上改变了生物学特别是医学的面貌。至少
自亚里士多德时代,哲学家和科学家们就一直认为自然发生说
(spohtaneous generation)解释了任何数量的生物现象出现的原因。这
也解释了为什么蛆虫会出现在腐臭的肉上,为什么有些植物可以在没有
种子的情况下发芽,为什么真菌会在腐烂的水果上生长。但是在19世纪
50年代进行的一系列巧妙的实验中,巴斯德表示,如果一个物体被适当
消毒,就不会出现自然发生现象。到1877年,科学家们确定了细菌会导
致人们患传染性疾病。这些微生物很快就被命名了。炭疽病是由杆菌引
起的,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细菌。不久之后,科学家们发现了咽喉部感
染、肺炎、麻风病等疾病的病原体
[25]。人们能够识别越来越多的细
菌,这种现象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在人们的热情和渴望中,科学家
们认定微生物是导致许多疾病的元凶。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些细菌实际
上是入侵弱化宿主的次生病原体。它们与疾病有关,但却不是病源。这
恰恰是人们在确定流感病因时犯的第一个错误。
1892年,两名在柏林工作的微生物学家声称他们已经发现了导致流
感大流行的细菌。他们称这种新细菌为流感杆菌(bacillus influenza)。
其他人将这种流感杆菌以其中一位发现者——微生物学家理查德·法伊
弗(Richard Pfeiffer)的名字命名为法伊弗氏杆菌(Pfeiffer’sbacillus)。当然,他们错了。这些流感患者身上肯定有细菌的存在,但
却不是形成流感的原因。相反,它们是一种继发性病原体。该继发性病
原体会入侵人们的身体,而此时人们的免疫系统已被我们现在所知的流
感病毒所击溃。细菌引起的流感并不比盘旋的秃鹰 杀死的鹿多,因为
狼才是鹿的主要死因。1918年,美国暴发了一场流感大流行。历史学家
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将法伊弗氏杆菌描述为“一个指
向错误的权威路标”
[26]。
今天,流感杆菌有了另外一个名称:流感嗜血杆菌(haemophilus
influenzae)。我曾多次为病人开抗生素来治疗这种令人讨厌的细菌,但
不明白为什么它的名字中含有“流感”这个词。它是肺炎、脑膜炎、耳部
感染以及更多疾病的元凶,但绝不是流感形成的原因。当我对流感相关
的混乱历史有所了解之后,其用词的不合理性就能说通了。这个名字来
自一个世纪前,而事实证明当时人们对流感的认知是错误的。
————
现在我们已经发现了这种病毒,但它具体是什么样子呢?是什么引
起普通感冒,让人多痰、流涕,为什么有的会变异成具有致命性的埃博
拉病毒?病毒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传播并折磨患者的呢?
进化,使病毒有别于我们体内发现的细胞。细胞含有微小的特殊器
官,而病毒没有类似的东西。由于缺乏线粒体,所以病毒无法制造能
量。病毒不含核糖体,所以它们不能构建蛋白质。病毒也缺乏输送废物
和毒素的溶酶体。这种病毒只是一个包含一束基因的框架,这束基因仅
仅是为了复制它们自身而存在。虽然计算机病毒的设计目的是为了让电
脑中毒并削弱或损害其功能,但大自然的病毒却并没有杀死细胞这个明
确目的。相反,它们唯一的目的是劫持一个细胞并把它当成一台复印机
来使用。为了做到这一点,病毒可能会伤害或破坏宿主细胞,但这只是
附带损害,而不是它们的首要目标。事实上,那些非常致命的病毒,可以在复制病毒之前杀死宿主细胞。流感病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和埃博拉病毒的致命 程度不同,但这些病毒采用的策略却是相
同的。它们入侵我们的细胞进行复制,然后必须寻找新的受害者来入
侵。病毒可能会让它们的宿主身体虚弱甚至死亡,但这是附带发生的。
我们现在已经认识了2000多种病毒,而且这个数量还在不断上升。
大多数医生只熟悉其中一些病毒。有一种疱疹病毒会致人患水痘(疱
疹)。而轮状病毒会引起幼儿腹泻。大约有100种不同的鼻病毒,这类
病毒会致使人们患普通感冒。还有像艾滋病病毒这样会导致人们患艾滋
病的逆转录病毒(retroviruses)。我们尤其对正黏液病毒
(orthomyxoviruses)这个有着笨拙名字的病毒家族感兴趣。“Ortho”一
词在希腊语中是“直的”的意思,而“myxa”的意思是“黏液”。正黏液病毒
家族包括流感病毒。实际上,有3种流感病毒株——分别为A、B和C,只有病毒株A和B能明显致人患病,而导致流感大流行的则是病毒株A。
流感是一种简单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病毒
[27]。它的形状像一个空心
球,内含8个病毒基因,由控制病毒功能的RNA(代替DNA)组成。
伸向外围的是两种重要的蛋白质,形状看起来像小小的穗状花序或
干草叉。尖尖的蛋白质被称为血凝素(hemagglutinin),或简称为
HA。在病毒被吸入肺部后,HA就会附着在细胞表面,这时,病毒的一
只脚已经迈入门内。细胞被诱骗,开始吸收病毒。一旦进入细胞,病毒
的包膜就会溶解并释放出8个基因,进入被入侵细胞的细胞核内。在那
里,它们强占了正常的细胞组织,并指导细胞制造数百万份的病毒颗
粒。然后,这些早期的颗粒回升到细胞膜内,就像沸腾的锅中的气泡一
样。由于被拴在表面,所以它们必须尽快摆脱束缚以入侵其他细胞。这
时,位于流感病毒表面上的第二个干草叉状蛋白质,被称为神经氨酸酶
(neuraminiolase)或NA,开始介入,并破坏细胞表面和病毒表面之间
的纽带。复制的病毒现在可以以 咳嗽或打喷嚏的方式自由地入侵另一名受害者。整个过程只需要几个小时,这些病毒就会离开被破坏的呼吸
细胞。那正是流感症状开始的时候。
在复制过程中,流感病毒可能采用两种方式之一发生改变,并且由
于这些变化,又产生了新的病毒株。如果构建新病毒的指令中存在复制
错误,第一种情况就会发生。这些指令被存储在8个病毒基因上,由遗
传密码构筑而成。当病毒复制时,该代码被读取并被复制数百万次。但
复制过程并不理想,因为其间会发生阅读或复制错误。因此,后代病毒
中的代码可能与亲代病毒的代码有所不同。遗传指令中的这些差异,导
致病毒表面的蛋白质发生了细微的变化。由于人类的免疫系统学会了通
过其表面上的蛋白质来识别流感病毒,因此这些细微的变化会导致免疫
系统无法识别流感病毒。这就是新病毒的发展方式,以及我们可能多次
感染流感的原因。从本质上讲,我们每次都会感染新的病毒。
要了解新病毒可能产生的第二种方式,我们必须明白甲型流感不仅
存在于人类身上,也会感染许多不同的物种,比如猪、鸟和马。有时,两种或更多种不同的病毒株会入侵同一肺部细胞。在那里,来自各个病
毒株的基因混合在一起并产生了一种杂交病毒,该杂交病毒含有来自双
亲的遗传物质。哺乳动物的肺部会感染流感病毒,而鸟类身上的病毒则
存在于肠道中。受感染的鸟粪可能含有数十亿的禽流感病毒,每种病毒
都可以与其他流感病毒株的遗传物质混合在一起,包括那些感染人类的
病毒的遗传物质。如果禽流感病毒和哺乳动物的流感病毒同时入侵一个
细胞,它们的基因就会混合在一起,从而产生一种全新的流感病毒。这
种新的流感病毒具有致命的杀伤力。这是1918年发生的事情,当时,鸟
类对这场流感大流行的生成、传播起到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1997年
在香港也发生过类似事件。一种新的禽流感病毒感染了与鸡有密切接触
的人。18名禽流感确诊患者中有6人死亡。只有那些直接接触鸟类的人
才会感染这种禽流感病毒,它在人与人之间并不相互传播。但只需要一
个小小的突变,病毒即可获得这种能力,从而为新的流感大流行做好准备。
虽然一个流感病毒就可以入侵细胞并繁衍数百万个后代,但实际上
只有为数不多的病毒具有繁殖能力。几乎所有发生的遗传变化都会损坏
病毒颗粒,致使其丧失繁殖能力。但鉴于感染流感后会产生数百万个病
毒颗粒,即使是成功率只有1%或2%,也会导致细胞中产生成千上万的
新型流感病毒并感染其他患者。
人类的免疫系统不断进化,已经可以预防和控制病毒、细菌和其他
外来病原体可能带来的感染。第一道防线由吞噬细胞(phagocytes)组
成,其名称来源于希腊语的意思“吞噬细胞”(devouring cell)。吞噬细
胞有点类似交警。它们总是在巡逻、侦察,发现、包围病原体,并将病
原体拉入细胞内,把它们消灭掉。吞噬细胞并不专门针对特定的细菌或
病毒。相反,吞噬细胞已经被编入人类的遗传密码中,以识别一般的病
原体。人类生来就具有这种先天性的免疫力,并且吞噬细胞无须事先接
触病原体就能够搜索、识别并破坏它。
人类免疫系统的第二道防线是抗原递呈细胞(antigen-presenting
cell)。这类细胞以特定的病毒或细菌为攻击对象。它们就像侦探,可
以描绘嫌犯的外貌。它们消化病原体并将其一些基本构成要素——例如
蛋白质或受体——呈现给另一种被称为辅助T细胞(helper T cell)的免
疫细胞。然后,这些T细胞大量增殖,并根据病原体的特征来确定相应
的敌人。与病原体首次相遇之后许多年,T细胞依然会记住它们的宿敌
并采取行动。这就是我们大多数人只患一次水痘的原因。我们与病毒的
第一次遭遇就会产生T细胞,这些细胞会永远保护我们。
人体始终会学着去抵御新的入侵者。疫苗接种就是利用了这一点。
通过向我们的免疫系统提供弱化的或无害的病原体,人体能够在感染疾
病之前制造抗体。免疫系统不在乎它是正常遭遇到病原体还是病原体通
过针头以疫苗的形式进入体内。无论哪种方式,免疫应答都是一样的。这样,下一次在身体遭遇病原体时,它能够更快更有效地对抗感染。如
果之前我们的免疫系统未能识别抗原,我们仍可能产生针对抗原的抗
体,但过程较缓慢。病情会越来越严重,持续时间也更长。在某些情况
下,如果无法对病毒立即发起攻击,可能会对人体产生致命影响。
流感会破坏人体精密的防御系统,因为它常常变换形态。流感经常
改变其表面的蛋白质,变得让人体难以识别。就像一个善于伪装的罪
犯,很容易就消失在人群中。这些变化为病毒提供了隐身衣,使得现有
抗体无法识别它们的存在。这就是你可能在某一季节中不止一次患流感
的原因:你的身体会产生针对第一种病毒的抗体,却会被它未能识别的
第二种病毒感染。这种“抗原漂移”(antigenic clrift)也是每年需要更新
流感疫苗的原因。病毒不断地变换外表,就像川剧“变脸”一样。
除了抗原漂移外,流感病毒还会经历更大的变化,即“抗原转
变”(antigenic shift),这正是人类患流感大流行的原因。在抗原转变期
间,病毒蛋白质呈现一种全新的结构。据说这种病毒很“新颖”。这些新
型病毒——通常在动物和人类病毒共享并交换它们的基因时出现——它
们就类似于新的罪犯,而不是伪装的老罪犯。所以这种新型病毒更狡
猾、更高产,也更致命。由于抗原转变,产生了致命的1918年流感病
毒,导致了2009年猪流感爆发。
通过漂移、转变、共享基因,流感的变形速度超过了人体识别它的
速度。在免疫系统开始产生针对一种病毒株抗体的过程中,不同的流感
病毒株会产生并演变成致命病毒。流感病毒的发展已经比我们的免疫防
御系统领先一步。
1918年的新病毒让数千万人丧命。关于这次流感流行病的第一份报
告来自欧洲。当年6月份的一份医疗报告很短,而且大部分内容含糊不
清,却对疫情暴发的位置进行了详细地描述:1918年5月28日,在西班牙的瓦伦西亚出现了一种性质不确定的疾病
[28]。这种疾
病的特点是患者发高烧,但是持续时间短,并且伴有类似于流行性感冒的症状。西班
牙的其他城市也发现了多例疑似病例。
接下来的一个月,在欧洲战事之外,《纽约时报》报道指出,一种
新的疾病——“西班牙流感”
[29]
,“在整个德国前线广泛传播”……这种
疾病妨碍了进攻战斗的准备工作。“无一人具有免疫力。在1个月之内,德皇本人也得了这种疾病
[30]。就像训练有素的军队一样,流感似乎有
自己的战术战略。但是这种战术战略极为隐秘。它不止一次袭击了所有
的战线。而第一批深受其害的人是士兵,他们曾经期望能参与一场别开
生面的战斗。”
[1] E. Rybicki,“The Classification of Organisms at the Edge of Life,or Problems with Virus
Systematics”,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Sciences 86 (1990):182-98.
[2] M. Emerman and H. S. Malik,“Paleovirology—Modern Consequences of Ancient
Viruses”,PLoS Biology 8,no.2 (2010):e1000301.
[3] Sally Smith Hughes,The Virus:A History of the Concept (London: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Science History Publications,1977),109-14.
[4] “……让牛痘病毒变得特别与众不同的是,一旦感染了牛痘的人在康复之后就不会再感
染了。”Edward Jenner,An Inquiry into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the Variolae Vaccinae,a Disease
Discovered in Some of the Western Counties of England,Particularly Gloucestershire,and Known
by the Name the Cow Pox (London:Sampson Low,1798),6. 我们在第九章里会再次提到詹纳
(Jenner).
[5] Hughes,The Virus ,112.
[6] Hughes,The Virus ,114.
[7] A. D. Langmuir et al.在以下文章中引用了这句话:“The Thucydides Syndrome. A New
Hypothesis for the Cause of the Plague of Athens”,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13,no.16
(1985):1027-30.
[8] Francis Adams,The Genuine Works of Hippocrates (New York:William Wood,1886),298.[9] Charles Creighton,A History of Epidemics in Britain ,2nd ed.,vol.2 (New York:Barnes
Noble,1965),328. 记录了咳嗽的更早期流行病学,就像发生在1658年4月的那场一样,然
而,流感常常是冬季特有的疾病,因此它也就不可能是4月咳嗽流行的原因。
[10] Charles Creighton,A History of Epidemics in Britain ,2nd ed.,vol.2 (New York:
Barnes Noble,1965),328.
[11] Charles Creighton,A History of Epidemics in Britain ,2nd ed.,vol.2 (New York:
Barnes Noble,1965),329.
[12] 1729年冬天的疫情流行起来特别粗暴,影响了英国、爱尔兰以及意大利。参见Charles
Creighton,A History of Epidemics in Britain ,2nd ed.,vol.2 (New York:Barnes Noble,1965),343页。不是所有大流行病都是流感。例如,在1743年4月有个流行病,当时“患者体温
升高时,皮肤常常发生红肿,随后,身体的大多数部位出现脱皮”,这不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病
毒性流感的描述,而更像曾经一度很常见的“猩红热”,是由链球菌感染所引起的。
[13] Lawrence Altman,“Is This a Pandemic?Define ‘Pandemic’”,New York Times ,June 8,2009,D1. See also D. M. Morens,G. K. Folkers,and A. S. Fauci,“What Is a
Pandemic?”,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 200,no. 7 (2009):1018-21.
[14] K. D. Patterson,Pandemic Influenza,1700-1900 (Totowa,NJ:Rowman and
Littlefield,1986),5.
[15] K. D. Patterson,Pandemic Influenza,1700-1900 (Totowa,NJ:Rowman and
Littlefield,1986),83.
[16] Henry Franklin Parsons,Report on the Influenza Epidemic of 1889-90 (London,Eyre and
Spottiswoode,1891).
[17] Henry Franklin Parsons,Report on the Influenza Epidemic of 1889-90 (London,Eyre and
Spottiswoode,1891),24-27.
[18] Henry Franklin Parsons,Report on the Influenza Epidemic of 1889-90 ,107页,在本书的
另外一处(第102页),帕森斯还引述了一个法国教授的观点:“流感是从俄国的土壤里滋生出
来的,而且这种疾病是悄无声息的,而非轰轰烈烈的。”帕森斯对这个说法表示怀疑。他指出,在俄国出现的情况和在欧洲其他地区出现的情况一样:“如果这种情况可以证明俄国有流感滋生
的土壤,那为何别处没有呢?”当我写这段话时,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正在调查俄罗斯对于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影响,这相当具有讽刺意味。还有没有什么事不会怪到俄罗斯头上的?
[19] Creighton,A History of Epidemics in Britain ,397-409.
[20] Parsons,Report on the Influenza Epidemic of 1889-90 ,70.[21] Parsons,Report on the Influenza Epidemic of 1889-90 ,82.
[22] Parsons,Report on the Influenza Epidemic of 1889-90 ,73.
[23] Parsons,Report on the Influenza Epidemic of 1889-90 ,102
[24] Parsons,Report on the Influenza Epidemic of 1889-90 ,106.
[25] Hughes,The Virus ,6-8.
[26] Alfred W. Crosby,America’s Forgotten Pandemic:The Influenza of 1918 ,2nd e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269.
[27] J. K. Taubenberger,A. H. Reid,and T. G. Fanning,“Capturing a Killer Flu
Virus”,Scientific American 292,no.1 (January 2005):62-71.
[28] “Undetermined Disease—Valencia”,Public Health Reports 33,no.26 (1918):1087.
[29] “Spanish Influenza Is Raging in the German Army”,New York Times,June 27,1918 .
[30] 在一句话的电讯中,该报纸称“德皇和皇后患有轻度西班牙流感”。“Kaiser Has
Influenza”,New York Times ,July 19,1918.3 来势汹汹: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
劳瑞·迈纳(Loring Miner)博士是美国堪萨斯州的一名乡村医生,他的医学实践完全不同于今天。他居住的地方离最近的医院也很远,在
当时难以想象会有现代的医学设备。尽管他所生活的时代存在技术局
限,但迈纳博士在1918年的流行病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18年,迈纳拥有了一间庞大的办公室。他在850平方英里的平坦
农田上进行乡村医学实践。这些农田由1720名潜在的患者进行种植和收
获。哈斯克尔(Haskell County)是堪萨斯州西南部的一块完整的土
地,位于威奇托(Wichita)以西200英里处。1918年1月和2月,农闲时
节,迈纳博士发现了数十例严重流感病例,他称之为“未确定性质的病
症”。仅在一天内,就有18人患病,并有3人死亡。在像哈斯克尔这样人
烟稀少的地方,这种现象是如此引人注目以至于迈纳博士给卫生官员写
了一份报告
[1]。这是第一份有关医生警告流感爆发的记录
[2]。虽然我
们尚不能确定,但哈斯克尔也许是1918年流感疫情在 美国乃至全世界
的着地点。
哈斯克尔以东300英里,是美国陆军所在的芬斯顿营地(Camp
Funston)
[3]。来自营地的士兵在流感疫情高峰期看望了位于哈斯克尔
的家人,并于1918年2月底返回基地。3月4日,芬斯顿营地的第一名士
兵患上了流感。随着士兵在芬斯顿营地以及其他军营和非军事领域之间
自由行动,病毒呈波浪形向外扩散
[4]。它首先抵达法国布雷斯特
(Brest),美军最大的登陆点
[5]
,并在该地进行传播。这些事实有力
地支持了1918年全球流感疫情源于美国中心地带的预测(但这只是一种预测)。
证据表明可能还有另外两个着地点。第一个是在法国。来自伦敦大
学的病毒学家约翰·奥斯佛(John Oxford)注意到,1916年,法国北部
埃塔普勒(Etaples)的英国军营暴发了一场流感。两个月后,在英国军
队的总部,位于英国奥尔德肖特(Aldershot)的一个军营爆发了几乎同
样的流行病,其中四分之一的患者因病死亡。医生注意到这场流行病与
法国暴发的流行病有诸多相似之处。两年后,奥斯佛指出,在很短的时
间内,有报道称在相隔很远的国家爆发了流感疫情。1918年9月至11月
[6]
,挪威、西班牙、英国、塞内加尔、尼日利亚、南非、中国和印度尼
西亚都受到了疫情的影响。当时国际航空旅行还没将世界连接起来,那
么病毒是如何得以迅速传播的呢?奥斯佛推理认为,肯定很久之前病毒
已“根植”于这些地方,也许是由1916年冬季第一次世界大战高峰期间返
回欧洲的士兵带回来的。
1918年流感病毒是源自法国的埃塔普勒营地还是其他地方,比如堪
萨斯州?约翰·奥斯佛拿出一组法国士兵与活猪、鸡和鹅接触的照片
[7]。他认为罪魁祸首是这些家禽,但这并不能证明它们就是病毒的来源。
病毒也有可能来自世界另一侧的中国。
1918年6月,《纽约时报》报道称“一种奇怪 的类似于流感的流行病
正席卷中国的华北地区。
[8]”报道称大约有2万例新增病例。疫情暴发的
时间比欧洲和美国疫情暴发的时间早几个月
[9]
,但死亡人数相 对较
少。由于之前接触过类似的病毒,人们似乎有了一定的免疫力。是1918
年流感的前身已经在中国传播了好几年然后发展成为全球流行性疾病的
吗
[10]?从中国到法国,肯定有病毒传播的途径。在战争期间,超过14
万名中国劳工被招募到法国
[11]
,许多人驻扎在蒙特勒伊(Montreuil)
附近,距离英国军队的埃塔普勒营地
[12]
不足7英里。在全球范围内,人
类大规模的迁移,对于活跃的病毒来说是个好消息。在1918年,随着欧洲战争进入第4个年头,许多国家对新闻报道进
行了审查,特别是那些有关流行性疾病的报道。有关战争的诸多坏消息
却没有进一步使焦虑的公民和士兵消沉。整个战争期间,西班牙仍然是
一个中立的国家,因此其媒体可以自由报道新的流感疫情。这使人们认
为迈纳博士的“性质未确定的疾病”就是从那里传播的。虽然今天的科学
家仍然在梳理病毒起源理论,但至少所有人都同意一点:所谓的“西班
牙流感”的最早暴发地肯定不是西班牙
[13]。
那么,1918年的病毒从哪里开始的呢?是从哈斯克尔,法国还是中
国?知道这一点可能有助于防止将来暴发类似的疾病,但我们仍然没有
弄明白病毒究竟是从哪里开始的。每一种理论都有证据支持,但随着
1918年流感大流行逐渐淡出历史,我们不太可能得出明确的结论。这种
变化、这种不确定性、这种神秘感是流感危害人类的特征。
与病毒的起源和传播路径一样重要的是有关病毒破坏性的细节。人
们尚未研发出治疗流感的方法或对抗流感的抗生素,而且流感带来的后
果极为严重且难以预测。这种病毒是如何传播的?它具备什么能力?我
们从血腥的欧洲战场上可以找到这两个问题的答案。
病毒发起了两波攻击
[14]。第一波攻击开始于1918年春天,当时有
超过11万名美军士兵被调遣到欧洲战线。自英国向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
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年半。战争席卷了整个欧洲。伍德罗·威尔逊
总统在1914年宣布美国会严格遵循“中立”政策。但随着德国潜艇瞄准了
美国船只,这种局势越来越难以维持。从1917年开始,美国陆军带着大
批年轻人穿越大西洋来到大型的狭窄营地。这些营地为流感病毒的传播
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至1918年夏天,这种拥挤不堪的局面极具致命性。
流感已经发生变异,年轻人尤其会有患病的风险。在巨大的病房里,士
兵们躺在那里彼此触手可及,隔开他们的只是一张悬挂着的床单。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感染率相同的情况下,入伍士兵的死亡人数远远多于平民。大多数生病的士兵被转移到这些拥挤的病房。在那里,又
繁殖出了一种细菌
[15]
,这种细菌能衍生致命的继发性感染。这些病房
非但不能让患者恢复健康,反而成了繁衍疾病的大型培养皿。
美国第16 综合医院红十字会病房,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1918年
病毒不只在营房和船上的医务室传播。在欧洲,成千上万的人在家
乡、军营、码头和战争前线之间来回穿梭。美国战争部门每月向法国派
遣20万人。到了夏天,在欧洲作战的美国士兵就有100多万人。
我们不知道在流感第一波攻击中有多少平民患病之后死亡。当时,对医生报告有关流感的情况,没有做任何要求。已成立的国家或地方卫
生部门很少,而那些现存的机构往往管理不善。但是,通过查看军方保
存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对当时发生的情况有所了解。从1918年3月开
始,堪萨斯州的芬斯顿军营内的流感病例突然增加。在卧床休息并服用
阿司匹林后的两三天,大部分士兵病愈。但有200人感染了肺炎,其中大约有60人死亡
[16]。在一个拥有4.2万人的庞大军营中,这些数字并不
足以引起军医的注意。
欧洲的情况更加糟糕。一名医务人员注意到,他所在的部队流感肆
虐,以至于士兵们无法行军
[17]。到了春天,美国第168步兵团大约90%
的士兵患有流感。到1918年6月,流感已扩散到法国和英国部队。返回
英国的英国士兵中,患有流感的病例超过了3.1万人
[18]
,比5月增加了6
倍。报道称,在欧洲大陆,20多万名英国士兵无法参战
[19]。病毒继续
通过海路进行传播。8月,英国轮船抵岸后,200多名船员罹患流感或患
流感后恢复。之后,病毒袭击了塞拉利昂的弗里敦。在不到一周的时间
里,病毒已经在陆地上蔓延;在9月底前,当地约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已
经感染病毒,其中有3%的人死亡
[20]。在孟买、上海、新西兰有关疫情
暴发的报道也开始见于报端。
第一波疫情有些温和。虽然有许多人患病,但疾病只持续了两三
天。几乎人人得以康复。像通常,婴幼儿和老年人感染病毒的风险最
大,死亡率远高于一般人群。但是,通过检查死亡记录,流行病学家注
意到,青年人和中年人的死亡率呈上升趋势,死于流感的比例较高。
当绘制流感死亡人数与年龄的关系曲线图时,我们最常见的是U形
图。U形图中的一臂代表婴幼儿,另一臂则代表老年人。在这两个年龄
段之间,死亡人数很少。1918年早期的流感死亡曲线图形状呈W状。两
端的死亡率仍然很高,但代表青年人和中年人的曲线也在升高。受影响
最严重的人群,年龄在21岁至29岁,通常情况下这群人被认为最不可能
死于传染病。这一现象很奇特,也令人震惊。依据年龄段划分的流感和肺炎的特定死亡率,包括1911-1915年流感大流行期间(虚线)和
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期间(实线)的死亡率。特定死亡率是指各个年龄段人口中每10万人的
死亡人数。
[21]
当欧洲大陆遭遇第一波流感袭击时,流感在美国几乎消失殆尽。随
着时间的流逝,在欧洲,感染流感的人数也在减少。到1918年7月,《英国医学杂志》称流感已不再对人类构成威胁
[22]。但在大西洋两
岸,最糟糕的情况却即将来临。
————
也许病毒已经变异成一种更致命的形式。也许是秋天拉近了人们之
间的距离,所以他们更容易相互感染病毒。无论如何,另一波流感开始
了。
有关第二次流感浪潮的最早的报道来自波士顿以西约30英里的德文
斯(Devens)营地
[23]。该营地能够容纳约3.6万名士兵,实际驻扎的士
兵已超过4.5万人。疫情始于9月8日左右,并迅速蔓延。每天有90名患
者来到营地医务室就医。之后,这一数字增加至每天500名,1000名。医务室很大,可以接待多达1200名患者。但很快,医务室的空间就明显
不足了。最终,它收容了6000名流感患者。一张床挨着一张床,一排接
着一排。
“我们吃饭、生活、睡觉、做梦都离不开病毒,更不用说每天有16
小时在吸入病毒。”一位年轻的医疗勤务兵在标有1918年9月29日字样的
信中写道
[24]。他被分配到一个150人的病房,而他的名字,罗伊
(Roy),是我们知道关于他的全部材料。流行性感冒(Grippe)——
流感的另一个名字——是所有人都可以思考的事。一个超级营房很快变
成了太平间,穿着制服的死亡士兵被摆放成两排。专门的列车有计划地
将死者运走。连续几天都没有棺材。罗伊写道,堆积起来的尸体“让人
感到疾病的凶残”。这位勤务兵目睹了无数人的死亡,他描述了罹难者
的遭遇。虽然这次的疾病始于另一流感病例,但这次的感染迅速发展成
为“从未见过的最严重的一种肺炎”。营地每天约有100人死亡,其中包
括“无数的”护士和医生。罗伊写道:“这比战后法国的衰败场景更加凄
凉。”他目睹过破坏力巨大又混乱的一战,但与疫情的破坏力相比,一
战的破坏力显得有些逊色。流感疫情更加糟糕。
密歇根大学医学院的著名医生兼院长维克多·C.沃恩(Victor C.
Vaughan)提供了另外一位目击者对德文斯营地大屠杀的描述。在他的
回忆录中,他记录了萦绕在脑海的可怕的场景,“我想清除并毁掉这些
记忆,但这超出了我的能力。”其中一个回忆录与德文斯营地分院有
关。他写道:“我看到数百名身穿制服的年轻、强壮的男子按10人或更
多人一组来到医院的病房。”“他们被安置在婴儿床上,直到每张床都睡
满了人,还有其他人挤进去。他们的脸色青紫,痛苦地咳嗽,然后咯出
了带血的痰。早上,尸体像薪柴一样堆积在太平间周围。”沃恩为自己
无法治疗瘟疫而感到惭愧。他总结道,“这种致命的流感,”“证明在破
坏人类生命方面,人类的干预毫无作用。”
[25]疫情开始不到一个月后,德文斯营地的流感疫情已经导致1.4万人
患病,750人死亡
[26]。流感也席卷了其他军事基地。比如,新泽西州的
迪克斯营地(Camp Dix)、堪萨斯州的芬斯顿营地(Camp Fuston)、加州和佐治亚州的营地。在纽约的厄普顿营地(Camp Upton),将近有
500名士兵死亡。流感于9月12日由2名服务员传播到爱荷华州的道奇营
地(Camp Dodge)。6周后,该营地有1.2万多名男子被感染。医务室一
度容纳了8000多名患者,是其最大容量的4倍
[27]。
每个营地暴发的疫情都遵循一种模式。首先,只有少数人患病,这
些患者与常规流感季的患者没有区别。接下来的几天内,病例呈指数级
增长,会有数百人感染,有时甚至数千人。在3周内,医务室人满为
患,死亡人数在增加。5-6周后,瘟疫就像它到达时一样神秘地消失
了。一些患者患有肺炎,但没有新增病例,生活慢慢恢复正常
[28]。
由于军方的需要而保存下来的记录,让人们对军营暴发的流感有了
更多的了解。但第二波流感不但袭击了军营,也导致美国各城镇数万人
殒命。这一波流感的综合杀伤力更具挑战性。当这波流感在1919年春末
消退时,美国平民和服务人员的死亡人数达到了67.5万人
[29]。巨大的
死亡人数令人震惊,疾病的传播速度令人无法想象。几乎每个城镇都受
到了疾病的冲击。
————
1918年,费城的人口超过170万。就像20世纪初大多数正在发展中
的城市一样,费城居民大多居住在狭窄的公寓里。他们特别容易感染流
感,因为费城的大多数 医生和护士都在国外,往往都受过伤并且厌
战。随着流感来袭,留在城镇的少数医疗专业人员因为劳累而身体瘦
弱。他们没有为即将发生的事做好准备。
流感可能于1918年9月中旬传播至费城,当时报纸报道称病毒正从军营向平民社区迈进
[30]。有传言说是德国装载细菌的潜艇导致了疫情
的暴发
[31]。事实并非如此,罪魁祸首很可能是费城海军造船厂。
该船厂有4.5万名船员并发展成为美国最大的海军基地。1918年9月
7日,该基地接待了300名从波士顿换乘的水手。很可能其中一些人身上
潜伏有流感病毒。2周后,900多名船员生病了。基地官员在讲话稿中写
道: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流感只不过是以新名字
[32]
伪装的平常的季节
性细菌。
但这种病毒即将在很大程度上向平民发起攻击。在病毒传播方面,战争债券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1918年4月,纽约市
举行了一场巨大的自由债券大游行。电影明星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
(Douglas Fairbanks)向肩并肩的游行群众发表讲话。凭借出众的外表
和迷人的个性,他号召群众购买债券以支持战争。5个月后,费城也加
快了敦促群众购买债券的步伐。《费城问询报》(Philadelphia
Inquirer)的一篇文章称
[33]
,该市计划在9月28日星期六为第4次自由贷
款运动的发起举行盛会。预计会有3000名战士参加,“如果需要的话,还会有女性士兵参与该活动”。数百名工人和司仪将与他们一起参加这
个活动,他们会让群众一起唱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流感疫情肆虐期间
进行的。有人担心如此大规模的聚会会促进流感的蔓延,但这种担忧被
人们的爱国热情所淹没了。
战争债券游行活动本质上是流感的行进乐队。当大量的群众沿街观
看并不断欢呼时,海军军人们也来到了百老汇街。
“这是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盛会,”
[34]
《问询报》称,估计有10多
万人聚集在街道上。随着人们伸展脖子以便看得更清楚,他们也顺带把
流感病毒传染给了别人。自由债券大游行活动实际上释放了这种病毒。
辉煌的游行刚刚过去两天,每天就有100多人死于流感。在短期内,这些数字增长了6倍。卫生官员每天都宣布疾病已经过去了,不料
下一次又发布了更严峻的统计数据。费城公共卫生部部长威廉·克鲁森
博士(Dr.William Krusen)下令关闭学校、教堂和剧院。如果他禁止自
由债券游行,情况也许就不会变得那么糟糕。各处张贴的布告提醒大家
不要在街上随地吐痰。但这并没有起多大作用。仅在一天的时间内,就
有60名随地吐痰的人被逮捕。
海军档案馆
由于生病人数过多,法院和市政办公室关闭,其他基础服务机构因
为没有了员工在苦苦支撑。警察和消防部门因人员减少而难以正常运
转。由于严重缺少员工,宾夕法尼亚州贝尔电话公司(Bell Telephone
Company)宣布只能处理那些“疫情或战争所需”
[35]
的服务电话。由于
正规医院超负荷运行,费城还创办了一所急诊医院。一天之内,500张床位都住满了病人。克鲁森呼吁人们保持冷静,并告诉公众不要因夸大
的报道而感到恐慌,但费城正遭受瘟疫的蹂躏,又有谁能做到处乱不惊
呢?
费城唯一的公共太平间只能容纳36具尸体。但这所太平间很快就堆
了数百具尸体,大多数尸体只覆盖着血迹斑斑的床单。每弄到一副棺
材,就有十具尸体在等候着。死尸散发的恶臭无处不在。当地的木工放
弃了正常的生意,开始专职做棺材。一些殡仪馆的收费标准增加了
600%以上
[36]
,导致该市将增长上限设置为“只有”20%。
在10月中旬,费城的死亡人数达到了顶峰,然后,瘟疫几乎与它来
临时一样突然消退了。当然,流感仍然存在,但因流感死亡的人数回落
至以往的水平。这个城市慢慢恢复了以前健康的模样。
费城发生的疫情在美国和世界各地重演。在旧金山,流感在10月也
达到顶峰。当月有1000多人死亡
[37]
,几乎是平常死亡人数的两倍。流
感向阿拉斯加的朱诺(Juneau)传播。该市试图通过强制检疫来阻止疫
情蔓延2
[38]。州长下令所有下船乘客必须接受码头医生的检查。任何出
现流感症状的人都不许进入朱诺。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阻止那些携带
病毒但尚未出现流感症状且看起来依然健康的人进入。几天后,这些病
毒携带者离开西雅图并停靠在朱诺码头,他们仍处在流感的潜伏期内。
当他们抵达码头时,由等待的医生对其进行简要的体检。如果医生发现
他们没有流感的征兆,就允许其进入朱诺。这是病毒潜入的最可能的方
式。病毒从朱诺传播到诺姆(Nome)和巴罗(Barrow)以及居住在数
十个偏远村庄的美洲原住民。与其他地方相比,流感在部落内的破坏性
更强。这些部落与其他人群处于自然分离状态,因此缺乏流感抗体。在
1918年流感暴发期间,位于阿拉斯加西部,拥有300名人口的小镇威尔
士(Wales),有一半人丧生。在布雷维格(Brevig Mission)的小型聚
居地,居民有80人,但只有8人幸免于难。1918-1919年纽约、伦敦、巴黎和柏林的流感死亡率曲线
[39]
从长远来看,北极圈附近发生的 这些恐怖事件有助于人们在不久
的将来对抗这种病毒。死者被埋在寒冷的土地中。这个永冻层安息地,掩埋并保存了死尸,使得80年后的科学家们能够提取1918年病毒的样
本,并首次确定其遗传密码。但在当时,这些尸体还在等待,冻结在泥
土与时光中。
————
美国此时正在打两场战争。第一场战争是针对德国及其军事盟友。
第二场战争是针对流感病毒及其细菌盟友。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这
是一场针对细菌和德国人的斗争
[40]。
随着盟军在西部战线上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流感袭击了运送部队到
欧洲战壕的船只。在法国东北部的阿贡森林战役(the Battle of ArgonneForest)中,流感夺去了许多美国远征军士兵的生命。正如大战几乎笼
罩着欧洲每个国家一样,流感在整个欧洲大陆肆虐。在一个拥有1000名
新兵的法军基地中,有688人住院治疗,49人死亡
[41]。巴黎关闭了学
校,但剧院和餐馆却没有停业。尽管有4000名巴黎人死亡
[42]
,咖啡馆
仍在开放。流感越过了战壕线。德军也深受其害。“每天早上都必须听
取工作人员报告流感病例的数量,以及他们对如果英国人再次发起袭
击,德军存在什么劣势的抱怨。这是一件使人痛苦的事情。”
[43]
当时,一名德国指挥官写道。
在英国,这是一种“保持冷静并继续生活下去”的方式。我在伦敦出
生并在伦敦长大,即使现在大部分时间我居住在英国以外的地方,我也
知道要面对逆境咬紧牙关,这是我童年时就明白的道理。当祖母回忆起
1940年德国空袭伦敦期间从伦敦撤离的场面时,我曾在她的脸上看到过
这样的镇定、沉着。我认识到这是对上一代西班牙流感的反应。“保持
冷静并坚持下去”不仅是公共行为的一种指示,也是英国文化基因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
起初,报纸几乎很少谈及这种流行病,如果一定要谈,报纸会把这
些报道埋在内页。英国政府和富有同情心的媒体默认限制任何有关流感
的讨论
[44]
,目的是避免削弱公众士气。因为世界大战已经进入第4个年
头,人们已经厌倦了战争。对事实进行如实报道和维持士气之间的紧张
关系,在J·麦克奥斯卡(J. McOscar)博士写的一封信中有所体现
[45]。
这封信隐藏在《英国医学杂志》的最后部分。
“无论男人、女人,还是孩子都有亲人离世的惨痛经历,我们现在
经历的黑暗日子还不够多吗?”他写道,“如果在发布此类报告时能够更
谨慎一点,而不是尽可能多地收集让人沮丧的消息来扰乱我们的生活,这样岂不会更好?一些编辑和记者似乎应该休假。他们去休假越早,对
公共道德也就越好”[原文如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刊发这封信的刊物在同一期的头版刊登了一份
长达5页的有关流感的详细报道。该报道强调了大流行性疾病的破坏
性。报道指出,英国和法国军队暴发了灾难性的流行病
[46]。该流行病
横扫了整个军队,致使军队丧失了战斗力。
英国的首席医疗官似乎也不愿意打扰任何人的生活。他的建议很有
限
[47]
:戴上小口罩,吃得好点,喝半瓶低度葡萄酒。英国皇家医学院
(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并宣布该病毒不
再像往常那样具有致命性。在这一连串的事件中,英国人似乎无动于
衷。1918年12月,随着大流行性疾病的结束,《伦敦时报》评论
说,“自黑死病以来,没有哪场瘟疫像这场瘟疫这样席卷了全世界。也
许,从来没有哪场瘟疫比这场瘟疫影响的人更多。”
[48]
那年早些时候,《泰晤士报》的医学记者夸大其词地描述了这样一
个民族,他们“高兴地期待”
[49]
着流行疾病的到来。历史学家马克·霍尼
斯鲍姆(Mark Honigsbaum)认为,英国政府故意鼓励这种坚忍主义,努力培养国人蔑视德国敌军,同样蔑视暴发的流感。
无论英国人对这一大流行性疾病持何态度,在这场流行病中伤亡的
人数都是巨大的。当流行病消退时,超过四分之一的人被感染,有超过
22.5万人死亡
[50]。在印度(当时属于英国领土),流感更具有致命
性,死亡率高于英国10个百分点,印度军队的死亡人数是英国军队的2
倍,一共有大约2000万印度人因流感大流行而死亡
[51]。
接下来是澳大利亚、新西兰、西班牙、日本以及整个非洲国家。所
有人都遭受了苦难,全世界共有5000万至1亿人因流感而死亡,人们对
近乎世界末日的猜测感到无比的恐惧。在大规模死亡之后,当公众关
心“这场流行病是如何形成的?”和“多少人受害?”时,科学家们不禁要
问:“为什么?”是病毒本身,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导致流感具有如此大的杀伤力?我
们已经找到了致使这么多人死亡的4种不同的解释。每种解释都有一些
证据支持,但没有一种解释是完全令人信服的。
第一种解释是
[52]
,病毒表面有一种蛋白质可以阻止干扰素的产
生。该干扰素向我们的免疫系统发出信号,表明我们的防御系统已被渗
透。将氧气转移到血液中的健康肺细胞,被病毒劫持,并在病毒复制过
程中遭到破坏。一旦这些健康的肺细胞死亡,它们就会被无法输送氧气
的暗淡的纤维状细胞所取代,就像在切割口部位形成的疤痕一样,看起
来与周围健康的皮肤不一样。几个小时内,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名叫罗
斯科·沃恩(Roscoe Vaughan)的美国陆军士兵被尸检。尸检表明他的肺
部有这种类型的肺炎。干扰素的破坏有可能使1918年的病毒引发致命的
病毒性肺炎。
第二种解释是,如果1918年的病毒本身不能致人死亡,那么继发性
细菌性肺炎可能会杀死人。大流行性疾病患者的身体变得虚弱,他们的
肺部已经被破坏,会感染链球菌(streptococcus)和葡萄球菌
(staphylococcus)等。在抗生素尚未研发出来的年代,这种情况是致命
的。我们现在认为,1918年大流行中的大多数患者是由这些继发感染导
致死亡的,而不是流感病毒本身。南卡罗来纳州士兵的肺提供了这种感
染的证据。他死于病毒的连续攻击,以及伴随着身体防御体系崩溃而至
的细菌感染。
对1918年流感杀伤力的第三个解释是,流感病毒引发了过度的免疫
反应,这种反应开启了对身体的自抗。假设你割伤了手指,细菌入侵并
感染伤口。由于血液流量增加,你的手指会肿胀、发红、变热,从而提
供更多白细胞来对抗细菌。其他类型的细胞因子信号蛋白会对这种对抗
感染的痛苦但必要的过程进行调节。一旦克服了这种感染,细胞就会停
止生产细胞因子,并且免疫系统会恢复以往的警惕状态。许多1918年的流感患者没有恢复正常。他们的肺被“细胞因子风
暴”(cytokine storm)
[53]
——过量生产的信号蛋白所击中。在细胞因子
的繁荣期,它们开始入侵并摧毁健康的细胞。当细胞因子风暴来袭时,免疫反应就会失控。细胞因子风暴激活了更多的免疫细胞,免疫细胞释
放出更多的细胞因子,细胞因子又激活更多的免疫细胞,这种循环周而
复始。大量的液体从饱受战争蹂躏的人们的肺部涌出。肺部的健康气囊
结痂。呼吸变得越来越难。
目前还不清楚为什么这场风暴发生在一些患者身上而其他患者却没
有,或为什么在20~40岁的人群中更为常见。传染病专家称这是本次大
流行最大的未解之谜
[54]。如果我们能够解开这个未解之谜,或许能够
保护自己不受另一种致命的流感瘟疫的伤害。
第四个解释指向了与流感传播有关的环境。它由一种源于鸟类的新
型病毒引起。在对人类构成威胁之前,病毒先在另一个宿主(可能是猪
或马)身上寄宿一段时间。当人们同时生活在一起——住在公寓或军营
里——并且异常流动的时候,病毒开始对人类的健康构成威胁。因为大
战使受感染的士兵们不断转战于欧洲及其他地区。工薪阶层家庭共用床
铺。士兵们并排睡在婴儿床上,并且乘坐统舱船环游世界。如果没有人
类这些行为,流感病毒无论多么致命,都不会如此迅速地传播。
今天,流感致死率不到0.1%。几乎每一名患者都可以康复。在1918
年流感大流行中,大多数患者也都康复了,但死亡率却比以往高出25倍
[55]。在美国许多人死于1918年的大流行性疾病,当时人们的平均寿命
从原来的51岁降至39岁
[56]。1900-1960年美国人均寿命的变化,显示了1918年流感大流行的影响
[57]
1918年12月,在疫情中期,1000名公共卫生官员聚集在芝加哥讨论
疫情。在三个月内,瘟疫夺走了40万人的生命。有人已经预言,第二年
会暴发会更加致命的流感疫情。
与会者之一的乔治·普莱斯博士(Dr.Georg Price)在他的报告中描
述了当时的现状。读起来令人恐惧
[58]。
首先,医生承认他们不知道流行病的原因。“我们不妨承认是病毒
并称之为‘x’病毒”,普莱斯写道,“因为病毒缺乏一个更好的名字。”医
生们在患者的分泌物中发现了几种不同的微生物,但这几种微生物是致
病元凶还是受疾病磨的身体自身出现的“机会致病性劫持
者”(opportunistic hijackers)?(事实证明是后者)
与会者就一些事情达成了一致意见。传播疾病的任何病毒均能在喉
咙、鼻子和嘴巴的飞溅物和黏液中被发现。借助飞沫,病毒可以通过打
喷嚏、咳嗽以及从手到嘴的接触进行传播。因此,一位医生建议减少病
毒传播的唯一方法是让“每个病人都穿着潜水员的服装”
[59]。医生们也一致认为,如果患者从流感中康复,他就会出现一定程度
的免疫力。许多40多岁的人都幸免于难。当时的理论和现在的一样,认
为那些在1898年经历过严重流感的人,已经具备了针对1918年流感的免
疫力。
但是如何控制疾病呢?由于与会者普遍没有信心,会上展开了激烈
的讨论。尽管采取了预防措施,但流感已经蔓延,然后它突然意外地消
失了。当时大量群众佩戴着面罩,但这并不能保证大家一定能够得到保
护。许多卫生官员认为它们提供了 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这也许是事
实,但无论如何,采取安全措施,仍然有一定的用途。芝加哥的卫生专
员
[60]
明确表示了这一点。“这是我们的责任,”他说,“让人们免于恐
惧。忧虑比流行病更具有杀伤力。就我个人而言,如果人们想要在金表
链上装个兔子脚,并觉得这样能帮助他们摆脱恐惧的生理行为的话,我
愿意帮他们实现。”
官员试图收集患者和死者的数据,但许多州没有被要求报告病例。
疾病前线的医生们过于忙碌,以至于无法填写必要的文件。很多患者在
接受治疗之前就已经死亡。因此几乎无法估计死亡人数,或被感染之后
康复的人数。人们还没来得及计算患者的人数,病毒已夺走了患者的生
命。没有任何机制可以用实际的数字来描述怪异的瘟疫。
在17世纪瘟疫期间,伦敦许多受疾病折磨的家庭在他们的前门上画
了一个大十字架,上面写着“主啊,请保佑这家人”。这个十字架警告着
人们,室内潜伏有疾病和死亡风险。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1918年,但是
以更加规范的方式——把“危险告示”张贴在门前。“危险告示”警告健康
人远离此地,在许多社区,几乎每家的门上都做过此类标记。
在公共卫生方面人们还做过一些努力,通过关闭学校、剧院、商
店,以减少公共场所的拥挤和混乱。这是一种迫使人们在休闲时间睡
觉、储存能量并避免感染的方法。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封闭措施是否奏效。底特律关闭了少量的公共场所,只有相对小面积的地区遭受了流感
袭击。而费城制定了更严厉的封闭政策,却并未有效地阻止这场灾难发
生。纽约卫生局局长罗耶·科普兰(Royal Copeland)改变了公共汽车和
地铁的时间表,以阻止 乘车时人员过度拥挤。他在城市周围安装了大
型标志,提醒公众不要吐痰。但他没有关闭学校和剧院。他认为,与其
让学生住在拥挤的廉租公寓,还不如待在学校里,在学校他们可以学习
如何保持健康
[61]。
普莱斯博士对1918年芝加哥会议的描述以号召人们采取行动而结
束。尽管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绝望情绪,但他坚持认为,结束流感疫
情的最佳方法是借助于公共卫生政策。需要更好地协调各个卫生机构,这些机构应该像军队一样置于统一指挥之下。为了击败敌人,私人和社
区机构需与各级市、州和联邦共同努力。普莱斯知道他是异想天开,而
病毒无所谓。流感的诸多症状中,有一种症状比发烧或呼吸短促更致
命。这是一种无用的感觉,这种感觉对密歇根大学医学院院长维克多
·C.沃恩产生了终身影响。在目睹了这么多人的死亡之后,沃恩决心“再
也不要鼓吹医学院取得了巨大成就,要虚心承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无
知”。
[62]
————
关于1918年流感大流行的历史读起来令人沮丧。这就像看一部恐怖
电影一样。你知道凶手是谁,但你无法进入电影中的场景去拯救受害
者。但是,在大流行性疾病期间和随后的几年中,出现了源源不断的医
学发现,这使我们首次能够对流感进行还击。
一些医疗专业人员非常渴望查明导致流感的原因,他们将自己的生
命置之度外。1918年和1919年之间的那个冬天,在流感疫情高峰期,约
有3000万日本人患病,其中超过17万人 死亡。尽管如此,一位名叫T.山
之内(T. Yamanouchi)
[63]
的教授设法找到了52名主动充当人体实验对象的医生和护士。T.山之内教授从流感患者身上取下“痰液”,放入实验
对象的鼻子和喉咙中。有些人直接接触了这种被污染的液体,还有些人
在通过非常细密、可以过滤掉所有细菌的过滤器过滤后才接触它。这两
群人很快就出现了流感的迹象。于是,日本研究人员据此断言已知的细
菌不可能是造成流感的原因。此外,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这种疾病可以
通过进入患者的鼻子或喉咙来传播,这是我们现在认为理所当然但当时
几乎没有人认识到的流感特征。
一直有研究人员愿意把自己当作实验对象。澳大利亚医生巴里·马
歇尔(Barry Marshall)就是一个例子。他与合作者共同发现了导致胃溃
疡的细菌,被授予诺贝尔奖。为了证明这一点,马歇尔本人喝下了含有
细菌的污泥,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结果他患了胃溃疡。但是1918年的
这些日本志愿者的勇气更加引人瞩目。他们周围的流行病正在以前所未
有的数量夺去患者的生命,并且没有已知的原因或治愈方法。然而,52
名医生和护士同意接种从那些感染者身上提取的材料。他们准备做出最
后的牺牲。他们的勇敢和无私令人难以置信。
日本人的发现很快就被复制了。1920年,两名美国研究人员研发出
一种小型过滤器,可以滤除流感患者洗鼻液中的所有已知细菌。然而,当把剩余的物质注射到活兔体内时
[64]
,仍然能够在活兔身上引起类似
流感的症状。他们得出结论:细菌不是流感的成因。不久,有报道称
[65]
其他疾病是由于洗鼻液剂量太小而无法被过滤器过滤掉的细菌引起
的。流感大流行的原因仍然是一个谜,但我们已经排除了细菌的嫌疑
[66]。
那么,通过那些细菌过滤器人们得到了什么?当然是流感病毒。
1933年,伦敦北部一个实验室(离我长大的地方只有几英里)的两位英
国科学家证实,从患者喉咙里提取并过滤掉所有细菌的样本可以让雪貂
感染病毒。(事实证明,雪貂是为数不多的感染流感的哺乳动物之一。雪貂比猪更容易感染流感病毒。)这一研究是建立在日本人的实验结果
基础上的,英国科学家得出的结论
[67]
是“人类流行性流感主要是受到病
毒的感染”。在同一个十年内,人类取得的另一个重大进步是发现了可
以培养流感病毒
[68]。流感病毒被注入正在发育的鸡胚胎的羊水中,不
料对于相当挑剔的病毒来说这竟是一种理想的生长媒介。这是一项惊人
的重要发现。如果你能够种植病毒,你也就可以收集病毒、杀死病毒或
将其注入健康人群的体内,然后就得到了疫苗。
最后,在1939年,病毒学史上出现了分水岭。新发明的电子显微镜
拍摄了一张病毒图片。在历史上,我们第一次看到了罪魁祸首的样子。
到20世纪40年代,科学家已经分离出两株流感病毒(A株和B株)并开
始检测疫苗。其中一位科学家是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他后来
研发出脊髓灰质炎疫苗。在克里克和沃森于1953年发现DNA之后不久,人们就确定了病毒的各种构建块。之后,病毒学领域开始研发识别病毒
的工具和技术,并根据遗传成分对其进行分类。
医学是诊断和治疗疾病的艺术,也是防止历史重演的艺术。我们从
1918年的流行病中学到了足够的知识吗?已知的经验教训可以预防另一
场灾难发生吗?我们现在知道遇到了什么病毒,但我们能否更好地对抗
这种病毒?几十年后,当下一次大流行性疾病抵达中国香港时,世界再
次受到疾病的考验。
[1] “Influenza. Kansas—Haskell”,Public Health Reports 33,no.14 (1918):502.
[2] J. M. Barry,“The Site of Origin of the 1918 Influenza Pandemic and Its Public Health
Implications”,Journal of Translational Medicine 2,no.1 (2004):1-4.
[3] J. M. Barry,“The Site of Origin of the 1918 Influenza Pandemic and Its Public Health
Implications”,Journal of Translational Medicine 2,no.1 (2004):1-4.
[4] 有关芬斯顿军营流感暴发的整体描述,参见E. L. Opie et al.,Pneumonia at Camp
Funston”,JAMA 72,no.2 (1919):108-113.[5] Barry,“The Site of Origin of the 1918 Influenza Pandemic”;F. M. Burnet and E. Clark,Influenza:A Survey of the Last 50 Years in the Light of Modern Work on the Virus of Epidemic
Influenza ,monograph from the Walter and Eliza Hall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Pathology and
Medicine(Melbourne:Macmillan and Company,1942),70-71.
[6] J. S. Oxford,“The So-Called Great Spanish Influenza Pandemic of 1918 May Have
Originated in France in 1916”,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Series
B:Biological Sciences 356,no.1416 (2001):1857-59.
[7] J. S. Oxford,“The So-Called Great Spanish Influenza Pandemic of 1918 May Have
Originated in France in 1916”,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Series
B:Biological Sciences 356,no.1416 (2001):1857-59. 奥斯佛专门论述了病毒是否起源于中国
的问题。他认为这种可能性虽然不能排除,但“不太可能”(第1859页)。
[8] “Queer epidemic sweeps North China”,New York Times ,June 1 1918,1.
[9] Christopher Langford,“Did the 1918-19 Influenza Pandemic Originate in
China?”,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1,no.3 (2005):473-505;K. F.
Shortridge,“The 1918 ‘Spanish’ Flu:Pearls from Swine?,” Nature Medicine 5,no.4
(1999):384-85.
[10] 肖特里奇(Shortridge)提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至少在中国南方,在最早的流行病学
证据存在之前约50年,人类可能感染了一种类似H1的病毒。”
[11] Langford,“Did the 1918-19 Influenza Pandemic Originate in China?”.
[12] 肖特里奇援引林恩·麦克唐纳(Lynn MacDonald)的观点,称埃塔普勒附近有中国工
人。参见Lynn MacDonald,Somme (London:Macmillan,1984),189-93.兰福德(Langford)
对中国起源理论进行了详尽分析。他的结论是“1918-1919年,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发生了流感疫
情——尽管当时的健康状况普遍较差,但流感疫情在世界其他地方并没有那么致命。基于这一
发现,虽然奥斯佛和其他学者持有不同观点,我们可以认为1918-1919年流感病毒起源于中
国。”(“The 1918 ‘Spanish’Flu”,494)肖特里奇对这一理论持肯定态度:“我相信流感病毒来源
于中国南方,这符合该地区是大流行性流感病毒出现的地区的假设,并且它随着受经济驱动的
人口流动而扩散到广东省以外。”(“Did the 1918-19 Influenza Pandemic Originate in China?”,385.)
[13] 但这一名称已广泛流传。在关于1918年流感大流行的优秀历史著作中,阿尔弗雷德·克
罗斯比(Alfred Crosby)将此次疫情称为“西班牙流感”的次数至少为47次,尽管该书的第二版
于2003年发行。参见Crosby,America’s Forgotten Pandemic。理查德·科利尔(Richar ......
Academic Press (China)
INFLUENZA:The Hundred-Year Hunt to Cure the Deadliest Disease
in History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Dr. Jeremy Brown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Touchstone ,a
Division of Simon Schuster,Inc.
我们纪念战争,但其他极具破坏性的事件也应留置于我们的集体记
忆中。这个世纪是灾难、自然灾害、世界大战、疾病以及冲突不断的世
纪,也是一个大规模扩张、融合、全球化、技术突破和取得医疗成功的
世纪。流感大流行说明了这两个问题。人们的身体处于危险之中,而大
脑仍停留在舒适区。这是人类的失败,也是人类的胜利。
——杰里米·布朗 本书作者
杰里米·布朗是美国一流的急诊科医生,他创作了一本了不起的
书。从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到最近的流感爆发,讲述了一个个扣人心弦
的故事,从全新视角看待我们与流感的斗争。本书涉及广泛的研究,语
调幽默,它使我们不忘现代医学已取得的长足进步,也注意到每个流感
季我们仍面临的危险。——盖尔·达奥诺弗里奥博士 耶鲁大学医学院急诊医学系主席
流感是世界上最致命的疾病之一,《致命流感》用通俗易懂的方式
讲述了令人无比信服的相关故事。这本书非常及时,有趣,引人入胜,发人深省。
——大卫·格雷戈里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政治分析师,前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会见新闻界”节目主持人“流感是连
环杀手”,布朗从医学史、病毒学、诊断和治疗、经济学和流行病学、卫生保健政策、疾病预防等各个角度巧妙探讨了这种病毒感染。
——《书单》(Booklist ) 杂志重点书评
布朗追溯了流感病毒数百万年的历史、人们为了解并治疗它所付出
的努力,以及这种病毒的多次毁灭性爆发……这是一本扎实可靠的科普
书。
——《科克斯书评》(Kirkus Reviews )
布朗以这部讲述医学与流感长期斗争的可靠著作来纪念1918年西班
牙大流感结束100周年。布朗叙述了20世纪90年代为再现并在基因上解
码西班牙流感病毒所付出的“史诗般的努力”,这一举措不仅引发了人
们“所有这些修补都是在制造超级病毒”的担忧,而且凸显出了流感不易
把握的特性。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急诊科医生,布朗也就对抗该病毒提
供了广泛的建议。
——《出版者周刊》(Publishers Weekly )
谨以此书纪念以下逝者和生者
罗斯科·沃恩,纽约水牛城的士兵,1918年9月26日因流感病逝于南卡罗来纳的杰克逊营地。他的献身帮我们更好地理解了让他和其他数百万人丧生的流感病毒。
奥特姆·瑞丁格,她和流感抗争的故事是关于个人勇气和现代医学努力的宝贵一
课。
为了防止西班牙流感的传播,请在手帕里打喷嚏、咳嗽或吐痰。如果人人都能把
这个警示谨记于心,那就不会受到流感的威胁。
——费城蒸汽机车上贴的标语,1918年10月
就危险性而言,没什么比流感更厉害。
——汤姆·福里登,前美国疾控中心主任
2017年1月目录
前言 奥特姆的故事
1 灌肠、放血和威士忌:治疗流感
2 流感:病毒的前世今生
3 来势汹汹: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
4 “我会死吗?”:第二轮,第三轮,第四轮……
5 复活1918年的流感病毒
6 数据、直觉和其他战争武器
7 你的晚间流感预报
8 物资储备中的漏洞:达菲和尚未发现的治疗方法
9 寻找流感疫苗
10 有关流感的商业活动
后记
致谢
参考文献
索引前言 奥特姆的故事
2013年12月,奥特姆·瑞丁格(Autumn Reddinger)已经病入膏肓了
[1]。她的肺已经失去了功能。她的心脏也极度衰弱,已经无法将血液泵
到全身。唯一能维持她生命的是一台人工心肺机。她像个死人一样躺在
重症加强护理病房(ICU)里。她的父母已经喊来牧师为她做最后的礼
拜仪式。他们该如何向奥特姆独自抚养的孩子们解释他们的妈妈是死于
流感——一种常被忽视的小病?那位一周去两次健身房的有活力的年轻
女性如今一只脚踏进了鬼门关。
圣诞假期期间,奥特姆以为自己只是得了感冒,所以整个假期都硬
撑着和她的父母以及两个年幼的孩子待在西宾夕法尼亚的家里。两天后
她感觉好些了,就去和朋友乔共进了晚餐。回到家后,她就开始给乔发
短信。乔收到的短信杂乱无章、没有表达任何意思。她在晚餐期间行为
正常、思路清晰,而且乔知道她没喝酒。乔感觉不对劲,就连忙驱车前
往奥特姆的家,发现她已经神志不清、非常虚弱。他让她的父母看管好
小孩,然后开车将奥特姆送到了位于庞克瑟托尼的当地医院。奥特姆告
诉急诊室的护士她的肺正在燃烧。
急诊室的医生给奥特姆进行了一整套检查:用听诊器检查了她的双
肺,回音清晰;她的脉搏和血压正常;没有发烧;胸部X光片显示肺部
无感染;血相检测正常且流感快检结果显示阴性。但医生还是认为有些
不对劲,所以为了保险起见,让奥特姆先住院观察,并开始用抗生素。
奥特姆的状况迅速恶化。几个小时后,她变得越来越神志不清,且呼吸越来越困难。抗生素看起来没有起任何作用。该医院的工作人员给
2个小时车程之外的匹兹堡梅西医院(Mercy hospital)打了个电话。奥
特姆现在的状况很危急。用急救车运送,风险很高,所以梅西医院派了
架救援直升机来接她。直升机将奥特姆送到梅西医院时,她已经无法自
主呼吸。注射镇静剂后,医生给她插入了喉管,并连上了呼吸机。
奥特姆被直接送进了梅西医院的ICU。到此时,她咳血,呼吸机已
经无法给她输送足够的氧气以维持生命。胸片显示她的双肺(几个小时
前还是回音清晰且看起来完全正常)已经充满了脓液和体液。医生给她
用了更多抗生素,并连上了静脉输液,以防止她的血压进一步下降。凌
晨1点,ICU团队叫来了霍特·莫瑞医生,他受过专业的急诊科医师培训
且目前专职于重症监护。他是奥特姆最后的希望。
莫瑞是一名ECMO专家。ECMO,全称体外膜肺氧合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是人工心肺机应用技术。
ECMO机器把暗黑色的血液从人体里抽出来,去除二氧化碳,注入氧
气,再把鲜红的、健康的血液输回人体内。该技术常常用于心脏或肺移
植手术中。由于奥特姆的双肺彻底不工作了,所以需要该设备替代肺功
能。
当莫瑞告知病人家属要给病人上ECMO时,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可能只有几分钟来解释操作流程并得到他们的同意。“我认为我们别无
选择,”他说,虽然他非常小心谨慎,“ECMO或许可以挽救她的性命,但也会带来一系列副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家属往往很难做出明智的决定,他们往往高度依赖
医生,希望他能够告诉他们该怎么做。奥特姆的父母已经到了梅西医
院,同意ECMO计划。
很快,莫瑞将一根粗大的针头插入奥特姆的腹股沟血管中,将她的血液从体内引出,并送入机器清洗(去除二氧化碳),然后注入氧气;
另一根针头插入颈部血管,血液从此处回流到体内。ECMO能改善她体
内的含氧量,但并未持续很长时间。最后,她的心跳还是停止了。
莫瑞和他的团队(包括护士和医生)开始连续的胸外心脏按压,并
注射了一针肾上腺素来帮助恢复心跳。获得了短暂的成功。但很快又不
行了,继而注射更大剂量的肾上腺素。心脏复跳,但几乎无法行使正常
的功能。莫瑞对奥特姆的心脏做了超声,结果发现它的泵血能力不足正
常水平的10%,已经无法将血液泵至全身。
对于像奥特姆现在这种状况的病人,医生们会用一个相当让人不舒
服的词来形容——“无力回天”。用客观通俗的语言讲,这个词描述了在
挽救病人的每种尝试都失败后的无力感。奥特姆正在一步步走向死亡。
即使一开始奥特姆的流感检测呈阴性,但莫瑞医生还是用更灵敏的
方法重新进行了一次检测,结果显示奥特姆感染了H1N1流感病毒,和
2009年爆发的猪流感病毒一样。在几个小时内,病毒就摧毁了她的双
肺,现在正在攻击她的心肌。原来替代了她双肺功能的ECMO机器也不
足以维持她的生命了,现在还需要承担她衰竭的心脏的工作。为实现这
个目的,这台机器需要重新插管
[2]。这就需要将奥特姆转移至4个街区
以外的匹兹堡大学长老会医院(University of Pittsburgh’s Presbyterian
Hospital),在那里心外科医生可以做这个手术。莫瑞在救护车后车厢
里陪护着奥特姆,小心监视着便携式ECMO设备。奥特姆被直接送进了
手术室。外科医生用锯子锯开了她的胸骨,在右心房(心脏的4个腔室
之一)上插入导管,并将另一根导管直接插入动脉,然后重新缝合胸
骨。她的胸部留下了一条长长的垂直伤口,两个粗管子从伤口内延伸出
来,将奥特姆与人工心肺机连接起来。这是最后的办法了,莫瑞医生已
经没有办法提供更好的设备、更好的治疗方法或更勇敢的方案。她要么
挺过来,要么死去。奥特姆的父母,盖瑞和斑比以及他们的牧师一起坐在ICU旁边的家
属室里。“我们在一起,我们为她祈祷,”盖瑞说,“然后牧师告诉我
们,她看见了两个天使,还告诉我们会逢凶化吉的。”
牧师说对了。奥特姆的病情稳定了下来。她那颗被流感病毒打晕的
心脏在几天后恢复了正常。抗生素遏制了继发性细菌性肺炎。血压也没
再出现骤降。2014年1月10日,医生为她撤去了ECMO,虽然她还是无
法说话且需要连接呼吸机。1周后,她的状况进一步改善,可以撤去心
胸外科的重症监护设备。又经过1个月的缓慢恢复,2月13日,她从长老
会医院出院了,转到了她家附近的一家康复中心。她战胜了流感,但是
现在仍然有一场硬仗要打。在ICU里待久了的患者,身体常常会变得非
常虚弱。在康复中心,奥特姆不得不再次学习如何走路、如何爬楼梯,并进行一系列她过去认为理所应当、轻而易举的日常行为。经过两周的
严格训练,她离开了康复中心,返回家中。2014年秋天,在感染流感之
后的第9个月,奥特姆重返工作岗位。她的医疗费用将近200万美元,但
幸运的是,她有完善的医疗保险,个人只需要支付18美元。
她的颈部和胸部留下了伤疤。针管刺入腹股沟静脉造成的神经损
伤,使她到现在都无法弯曲左侧踝关节,左腿有时也会麻木。但是,她
的康复是现代医学的胜利。她被救了回来,因为她靠近一家有能力为她
提供当今最先进治疗措施的医疗机构。
如果奥特姆身处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有历史记录以来最严重的
一次流感大流行,她的命运将会截然不同。那时候最好的药物就是阿司
匹林,但当时这种药刚刚发明,常被误用致命的剂量。绝望和无视,产
生了大量稀奇古怪的治疗方法——从野蛮的放血疗法到毒气疗法。据估
计,那次流感大流行期间,有5000万到1亿人丧生。在美国,死亡人数
达到67.5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死亡人数的10倍。第一次世界大战
结束时,正是流感暴发达到顶峰之时。流感是我们在某个时间都曾经历过的东西:冬天的咳嗽、发热、身
体的疼痛和发冷,持续三四天,然后就消失了。作为一名急诊科医生或
者一名患者,我既有站在床边的经历,也有躺在床上的经历。我作为一
个病人到访急诊室的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经历,就是因为患上了非常严
重的流感。我发了高烧并开始神志不清。我已经虚弱到无法喝水也无法
下床,我的身体开始脱水。但即便是现代医学——可以把我从相对较轻
的感染中救回来,也可以把奥特姆从死亡边缘挽救回来——也不是万能
的。流感仍然是个连环杀手。
我们都满怀期待,希望看到癌症的治愈、心脏病的根除。我自然也
是有这个愿望的,但是作为一名急诊科医生,我还有个更朴实的愿望:
治愈流感。我们常会不经意地把流感当成一次严重的感冒,但是在美
国,每年会有3.6万~5万人因流感而丧生
[3]。这是一个让人震惊和绝望
的数字。但是还有更坏的消息,如果像1918年流感大流行时那么厉害的
流感毒株在今天的美国传播,那可能会造成超过200万人死亡
[4]。没有
其他能够想得到的自然灾害可以匹敌,并且流感不是人类做好预防工作
就可以防止它到来的。2018年早些时候,报纸上说当年的流感季是近十
年来最严重的
[5]。常常见到报道说年轻人、原本很健康的人死于流感。
有几家医院因为流感病人的涌入变得拥挤不堪,他们不得不支起分诊帐
篷或者把病人送走。
流感肯定不是“众病之王”——这是肿瘤学家悉达多·穆克吉
(Siddhartha Mukherjee)对癌症的描述——但它却可以发生在所有国
家。从文明出现曙光至今,流感就一直伴随着我们,它困扰着地球上所
有的文明与社会。
————
自1918年以来,我们对流感的几次大流行都有近距离的接触。1997
年香港暴发的禽流感没有使太多人丧生,但这只是因为150万只被感染的鸡全部被及时宰杀。2003年,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暴发,感染了至少8000人,其中10%的感染者丧命。最近我们又遇到了
MERS,即中东呼吸综合征,在2012—2015年感染了1400人
[6]。这种疾
病通过感染了的单峰驼传入人群。(在此给读者一个免费的医疗建议:
一定要饮用经过了巴氏消毒的骆驼奶。)这些病毒性疾病都起源于动物
宿主(目前认为)
[7]
,然后以某种方式传播进入人群——这也是1918年
的情形(目前我们是这么认为的)。我们不知道下次病毒大流行会在何
时何地发生,但我们可以确定它会发生。毋庸置疑的是,如果不早做准
备,那我们将会面对一个颇为艰难的局面。
1918年那场流感大流行之后的百年间,我们对流感有了更深入的了
解。我们知道了它的遗传密码,它是如何变异的,它是如何使我们生病
的,但是我们仍然没有有效的方法去战胜它。我们拥有的抗病毒药物用
处不大,流感疫苗的保护力也有限。在运气比较好的年份里,疫苗保护
的有效率只有50%,而2018年这个有效率的数字更低。疫苗只对大约三
分之一的接种者有效。
仅仅一个世纪,我们就忘了1918年那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它
是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疫情。在这期间,我们了解和掌握的知识足
以让我们畏惧并激励我们,但可能还不足以让我们有能力去阻止另一场
流感大流行的发生。正是由于它的神秘、变异和传播能力,流感成为人
类最强劲的对手之一。1918年的经验教训可能是我们唯一拥有的可以和
死亡结局抗争的免疫力。
[1] 奥特姆与流感抗争的细节来自多个电话访谈和我在2017年12月与奥特姆本人、其父亲、其医生霍尔特·莫瑞(Holt Murray)博士的邮件往来。
[2] 即由原来的股静脉引出颈静脉泵入的V-V ECMO变为股静脉引出颈动脉泵入的V-A
ECMO,或开胸手术后从左或右心房引出泵入动脉的A-A ECMO。——译者注
[3] “Estimating Seasonal Influenza-Related Deaths in the United States”,Centers for DiseaseControl and Prevention,2018年1月29日更新,http:www.cdc.govfluaboutdiseaseus_flu-
related_deaths.htm.
[4] 对1918年美国死亡人数的预估是基于1.03亿人口死亡67.5万人,今天美国有3.22亿人
口。
[5] Donald McNeil,“This Flu Season Is the Worst in Nearly a Decade”,New York Times ,January 27,2018:A15.
[6] 世界卫生组织“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MERS-CoV). Summary
of Current Situation,Literature Update and Risk Assessment”,2015年7月7日,可以从以下网址下
载,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1791842WHO_MERS_RA_15.1_eng.pdf.
[7] SARS可能是从果子狸(Himalayan palm civet)群体中开始流行的。这是一种真实的动
物,而且在部分国家和地区被食用。给读者一个免费的建议:远离狸猫类食物。参见W. Li et
al.,“Animal Origins of the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Insight from ACE2-S-
Protein Interactions”,Journal of Virology 80,no.9 (2006):4211-19.1 灌肠、放血和威士忌:治疗流感
我有很多嗜好,爱喝鸡汤是其中最糟糕的一个。当我还是个孩子的
时候,总是期待母亲在周五晚上可以给我做鸡汤喝。时至今日,我还记
得在伦敦长大的情形,以及伦敦那漫长多雨的冬夜。几个世纪以来,鸡
汤被认为是治疗咳嗽、感冒、发烧、寒战的土方——这些都是流感的症
状。母亲总是提醒我要把汤喝完,这样整个冬天就不会生病了。鸡汤是
我们可以想得到的最鲜美的预防性药物。
许多年后,我在伦敦的一所医学院校看到了一项研究,说鸡汤可能
真的有用。这篇文章发表在1978年的《胸科学》(Chest )杂志上
[1]
,文章的标题就像鸡汤那样鲜美:《饮用热水、冷水和鸡汤对鼻腔黏液流
速和鼻腔气流阻力的影响》。
在此项研究中,肺病专家让健康志愿者选择喝热水、冷水或热鸡
汤,继而检测鼻腔阻塞程度的变化——或者就像论文标题所说的,评估
流经鼻腔的黏液或气体的速度。研究者总结道,热水有助于疏通堵塞的
鼻子,鸡汤含有“一种额外的物质”可以使通畅程度更好。没人能够说得
清到底是 什么神秘成分,但研究者推测鸡汤里起关键作用的是蔬菜和
鸡肉的营养搭配。
内布拉斯加大学(University of Nebraska)医学中心的斯蒂芬·伦纳
德(Stephen Rennard)博士已经研究鸡汤十几年了。2000年,他通过对
他妻子的立陶宛祖母传下来的食谱进行研究,发现鸡汤中含有一种抗炎
症的物质
[2]
,可以通过抑制因感染而产生的某种白细胞的活动,从而减轻上呼吸道感染症状。
“可以确信无疑的是,100年后,我所做的其他事情都可能被人遗
忘,因为它们会变得和人们的生活无关,会过时,”伦纳德博士在一条
拍摄于自家厨房的YouTube视频里说道
[3]
,“但是,关于鸡汤的论文可
能仍然会被引用。”它的功效经过了医生的检验,得到了奶奶的认可。
有时候,古老的经验会带来临床上的成功。对于其他曾被用于治疗
流感的方案或药物,我也希望如此。灌肠疗法、水银疗法、树皮疗法、放血疗法等,都是一些你想不到且让你恶心反胃的方法。值得庆幸的
是,你不是出生在20世纪初。今天,一个合格的医生不会给你用这些方
法。但是就在100年前,它们却是当时最先进的方法。更让人震惊的
是,21世纪的今天,我们自认为最先进的方法也未必比过去那些显得粗
鲁的方法高明多少。
————
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卸任总统后不到3年,就躺在了他的
临终病床上。作为最后一种挽救他生命的方法,医生们切开了他的血管
以阻止感染摧毁他的咽喉部位。华盛顿经历了4次放血
[4]
,最后一次是
在他死前几个小时。
“我要走了。”华盛顿对他的秘书托拜厄斯·李尔(Tobias Lear)说。
“他死于缺血和缺氧。”华盛顿的朋友、家庭医生威廉·桑顿
(William Thornton)说。他甚至建议通过输羊血让华盛顿复活
[5]。
放血疗法就是把人体的血液、毒素和病原体排出体外,这是两千多
年来主流的治疗方法。在任何有用的药物或治疗方法出现之前,放血疗
法几乎是当时的全部了。这种方法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公元2
世纪的希腊医生盖伦(Galen)
[6]
的著作中曾提到这是一种可以治愈疾病的重要方法。放血疗法在《塔木德》(一本记录与犹太人法律和道德
相关的辩论的著作,成书于公元600年左右)中被多次提及,在中世纪
及其之前被广泛地应用。现在全球最著名的医学期刊之一《柳叶刀》
(Lancet )就是以放血疗法的主要工具命名的。
放血疗法从未成功过。事实上,它极其危险——问问乔治·华盛顿
就知道了。但是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里,这种方法仍然被用于治疗流
感,不仅限于非主流的医生,甚至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线军医也会推
荐使用,他们看到了另一个敌人——病原微生物——正在包围士兵们。
而且,这些医生还在权威的医学期刊上撰写了他们放血的经历,包括激
进的《柳叶刀》。
1916年12月,3位英国医生在法国北部服役,此时距离1918年流感
大流行还有大约2年时间。他们描述了一场席卷整个军营并导致灾难性
后果的疾病
[7]。这就像流感病毒正在进行一场预演,准备着下一步释放
更大的破坏力。医生们确诊这次的疾病是由流感杆菌引起的。并将其命
名为“化脓性支气管炎”,医生们还描述了他们如何努力治疗一个可怜的
患病士兵的失败经历。
“迄今为止,”他们写道,“我们已经无法找出任何对疾病治疗起作
用的疗法了。”然后还写道:“静脉切开术(即“放血疗法”)并未对这名
患者起作用,可能是因为我们没能早点有效地使用这种方法。”
如果你只是快速浏览了论文,很有可能就错过了这个信息——英国
医生试了静脉切开术,即“放血疗法”,但是这种方法并未奏效——他们
认为或许是因为他们试得太晚了。两年后,在流感大流行的高峰期,另
有几位英国军医也报道了给病人放血的病例,只有这次,至少在某些病
例中这种方法奏效了
[8]。
在20世纪,并不是只有英国人还在坚持给病人进行放血治疗。1915年,海因里希·斯特恩(Heinrich Stern),纽约的一名医生,出版了他的
著作《放血疗法的理论与实践》(Theory and Practice of Bloodletting)。斯特恩反对将放血疗法用于大多数疾病,但他确信这种方法对某些
疾病是有用的。
“我提倡有条件地使用这种古老的方法,”他写道,“但我并不将其
视为万灵药。”
[9]
在将放血方法推荐为流感一线疗法的问题上,斯特恩是有点矛盾
的。但就在差不多10年后,在美国的顶级医学期刊上,医生们仍然支持
用放血疗法治疗肺炎
[10]
,而且他们深信——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
下,当“我们更为保守的方法失败后”,放血疗法会成功。
用放血疗法治疗流感最终在20世纪退出历史舞台
[11]
,但是其他的
野蛮且让人生疑的方法仍然是医学计划的一部分。
————
1914年,一个名叫阿瑟·霍普柯克(Arthur Hopkirk)的医生出版了
一本黑色封面、烫金书名的小书——《流感:历史、自然、起因和治
疗》(Influenza:Its History,Nature,Cause and Treatment )。书里推
荐了一系列怪诞的流感治疗方法
[12]。对于发烧,霍普柯克医生推荐
了“大清洗”,即泻药,换个好听的名字叫“冒泡的氧化镁”。流感重症患
者需要效用更强的泻药,如升汞,这是由氯化汞制成的。众所周知,汞
是有剧毒的。
霍普柯克1914年的著作里确实包含了一些有价值的建议。例如,在
推荐升汞的同时,他还推荐了阿司匹林——从柳树的树皮里提取出来的
物质(当然今天阿司匹林仍然在使用,只不过你可能用的是泰诺或布洛
芬)。即便这是个有价值的建议,但还是过大于功,因为别的医生并不知道如何安全地控制剂量。阿司匹林过量服用后的症状是从耳鸣开始,继而出汗、脱水、呼吸急促,严重的过量服用会导致体液涌入双肺——
和流感的真实症状极其相似——继而进入大脑,然后脑部水肿,导致意
识混乱、昏迷、惊厥,甚至死亡。在西班牙大流感期间,很多人并非死
于流感,还有些人死于阿司匹林服用过量
[13]。
在流感大流行期间,阿司匹林广泛使用,但许多医生似乎并未注意
到它的危险。在德里,一些高年资医生担心在孟买和金奈的一些低年资
医生正在错误地使用该药物。在伦敦,一个在哈雷街(Harley Street,伦敦最著名的私人诊所集中地)行医的医生正大肆鼓吹使用该药物。他
建议给患者“灌阿司匹林
[14]
,剂量是每小时20格令
[15]
,持续12小时,然后每两小时给药一次”。这是最大安全剂量的6倍,是极其疯狂的阿司
匹林使用剂量。
许多人在流感大流行期间可能因服用了超高剂量的阿司匹林而不是
因为流感本身而丧生。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但是这或许可以解释
为什么有那么多健康 的年轻人死去
[16]
——这一人群在今天看来是很少
会被严重的流感感染的。
霍普柯克也建议肺炎患者服用“一茶匙复方安息香酊(Friar’s
balsam)
[17]
或一小撮桉树叶”,兑着1品脱
[18]
水喝下。复方安息香酊含
有安息香,是一种从几种不同的树皮里提取出来的树脂。我在急诊室一
直使用安息香,我会在包扎伤口前先在伤口周围擦上安息香,这样可以
使包扎更牢固。但是,它对治疗流感没任何作用。
霍普柯克,就像他那个时代的许多医生一样,也用奎宁(quinine)
来治疗流感
[19]。图片来自佛蒙特州报纸数码化项目
“在奎宁中,”他自信地写道,“有一种成分不仅可以控制与发酵有
关的发热进程,而且对流感病毒本身也具有一定的抗毒性作用。”
又是树皮。奎宁提取自南美的金鸡纳树(the cinchona tree)的树
皮。当地人用它来治疗疟疾。到17世纪中叶,它被传入欧洲,以“耶稣
会 士之粉”
[20]
(Jesuits’ powder)的名字(以当时将其带入意大利的宗
教团体的名字命名)为人们所知。直到10年前,奎宁还是治疗疟疾的一
线药物
[21]
,现在它在根除疟疾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么,它又
是怎么被用于治疗流感的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像流感一样,疟疾也会引起发热,而奎宁可以减
少发热频次,能有效缓解症状。如果奎宁可以治愈与疟疾相关的发热,为何不能将其用于治疗所有的发热呢?
[22]
所以,奎宁就成了对抗流感
的“武器库”里的标准化装备。当大流感发生时,奎宁在英国
[23]
、美国[24]
、欧洲大陆
[25]
被广泛使用。“Grove’s Tasteless Chill Tonic”是当时卖
得最好的奎宁产品。作为治疗疟疾的药物,这个产品使爱德文·威利·格
罗夫(Edwin Wiley Grove)在1870年年底一夜暴富。如今,它成为市场
畅销的治疗流感的药物。在全国的各类报纸广告上,这种奎宁水被宣称
可以“使人体系统变得强壮,可以用于治疗感冒、痉挛和流感,改善食
欲、让脸颊恢复红光、重获活力、净化血液,让人变得充满活力”。它
不仅有明显的“强身健体的功效”,而且不会引起胃部不适或者导致“紧
张或耳鸣”
[26]。
但是奎宁并不会像阿司匹林那样直接减少发热,所以它对于流感引
起的发热起不到作用。更糟糕的是,服用高剂量的奎宁
[27]
还会引起视
力问题,甚至导致失明、耳鸣和心律不齐。总之,对于流感而言,奎宁
是一种危险性高且毫无用处的药物。
对于霍普柯克收治的可怜的病人们来说,有毒的汞和树的汁液还不
是全部的治疗药物。对于因流感引起的恶心和呕吐患者,霍普柯克医生
还会给他们服用少量的干香槟(dry champagne)
[28]。
“对于感染了流感的病人而言,没什么比发出滋滋气泡声的香槟酒
更能唤醒他们的了。”
[29]
霍普柯克写道。
如果说这听上去还有点道理,那也只能局限在当时那个时代。即使
在100年前,医疗界也认为霍普柯克的建议是奇怪的。《美国医学 协会
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的一位匿名评论
员难掩蔑视地写道
[30]
:
国外的医生们,尤其是英国的,可能会将这么一本书视作可以接受的或者是富有
建设性的。但是对于广大美国人而言,从普通的教科书中就能获得相同质量的有用信
息,而不会通过持续不断地推荐无效的药物治疗来归纳推理。让我震惊的是,斯克里
布纳出版社(Scribner)居然同意出版这么一本书。确实令人震惊。但是霍普柯克的疗法并非你想象的那样不同寻常。
事实上,这些方法似乎相当主流(即使在美国,这让那个暴脾气的评论
员很是恼怒)。
关于我们如何与流感做斗争的,我最喜欢讲的例子就是1936年一个
流感病人的护理记录。这份记录被当成传家宝保存了下来,并在70年后
出版了
[31]。在3个星期的治疗里,这位病人经历了一连串惩罚性的安慰
剂治疗:芥末石膏粉(一种民间偏方,涂在皮肤上)、阿司匹林(治疗
发烧)、可待因(codeine,治疗咳嗽)、酚酞(phenolphthalein,一种
会致癌的泻药)、其他咳嗽药、樟脑油、7次灌肠(7次!)、直肠管
(别问做什么用)、镁乳(另一种泻药,求上帝快去帮帮他)、乌洛托
品(urotropine,一种尿道抗菌药),以及安息香酊。这个病人至少服用
了5次处方剂量的威士忌和14次蓖麻油。事实上,他的7次灌肠从医学上
讲是必须的,因为他至少服用了39次可待因,虽然抑制了咳嗽,但也会
引起便秘。
当时距离流感大流行已经过去了近20年,但仍然有病人在用修道士
的香脂和蓖麻油进行治疗。我们可以从霍普柯克1914年出版的书里和那
个接受了过度治疗的可怜病人的护理记录里总结出来的是,医生用了许
多民间偏方对付流感,这些偏方往好了说是没用,往坏了说就是有毒。
有些方子至少还是天然有机的:燃烧橘子皮、把洋葱切成丁来熏屋
子(灭菌)
[32]。许多医生 甚至自己配置药液和药物,并基于很难让人
信服的统计数据来推广它们。1919年2月,一位来自芝加哥的伯纳德·马
洛伊(Bernard Maloy)医生宣称,他已经治疗了225名肺炎患者,无1例
死亡
[33]。他使用了两种植物的酊剂——乌头(aconite)和绿藜芦
(veratrum viride),并用了10倍剂量的治疗方案。我们现在已经无从得
知每种成分的浓度,但是乌头(也叫monkshood)和绿藜芦(也叫false
hellebore或Indian poke)都是有毒的植物(如你所料)。一定剂量下,它们会引起恶心、呕吐和血压的断崖式下降,甚至有可能致命。马洛伊
的混合物肯定经过小心地滴定配置,以防出现副作用。我们不能忘记的
是,许多现代药物超过一定剂量也是有毒的。另外,他宣称这种混合物
可以100%预防或者可能阻断肺炎,这意味着,他的病人是被精心挑选
的,那些有着严重的流感或肺炎症状的病例被排除在了他的方案之外。
1918年流感大流行期间,有些人非常绝望,从而铤而走险,在没有
医生的指导下自己发明了充满危险的治疗方法。当流感恶魔在英国西南
部沿海小镇咆哮而过时,法尔茅斯的村民们并没有把他们生病的孩子送
去医院,而是带到了当地的煤气厂去吸煤气。家长们认为让孩子接触有
毒气体可以减轻他们的症状。
A·格雷戈尔上尉(A. Gregor),一位公共卫生官员开始通过观察法
尔茅斯不同人群的流感患病率来确认这种观点
[34]
是否科学。在一个海
军巡逻队基地,他注意到流感患病率为40%。在当地一个驻扎了1000个
连队的陆军军营里,患病率不足20%。在当地一个锡矿场,工人们暴露
于充满硝酸的毒气中,流感感染率只有11%。另外一些锡矿场工人暴露
于炸药和黑火药中,这些吸入毒气的“幸运儿”的流感感染率更低,只有
5%。
许多“脑子里的感冒”可以用烟气来治愈是一种流行的观点,这个观
点有“一定的事实基础”。格雷戈尔在1919年的《英国医学杂志》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上总结道。此时,流感大流行正在逐渐减
弱。他不是唯一一个持这种观点的人。另外一名医生的报告指出:“有
充分证据说明,毒气厂的工人们
[35]
实际上对流感有免疫力。”令人感到
欣慰的是,没人真的建议通过吸毒气来预防流感,即使是那个很喜欢升
汞的霍普柯克医生也没这么做。
格雷戈尔的发现是否真的和工人们暴露于毒气之中有关,现在已经
无从知晓。氯气确实可以杀死禽流感病毒,也有可能会杀灭煤气厂工人们身边飘浮着的流感病毒
[36]。但我们需要记住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期间,氯气以最残忍的方式杀死了许许多多的士兵。
————
并非所有医生都会像流感大流行期间的江湖郎中那样去给病人看
病。詹姆斯·亨里克(James Herrick)是一名在芝加哥工作的医生,曾就
读于伊利诺伊的拉什医学院(Rush Medical College),被公认为是一位
成功的医生
[37]。1910年,他是第一个描述后来被称为镰刀形红细胞贫
血症的人,尽管在当时,他还无法解释这种疾病的病因。两年后,他发
表了一篇关于冠状动脉疾病的重要综述,他认为这些动脉可能被堵塞,但不会马上致死。这和当时盛行的观点截然不同。基于经验,他成功地
描述了这些堵塞所引发的临床症状,比心血管造影技术出现整整早了1
个世纪。他的这些研究成果奠定了现代心脏病学的基础
[38]。此外,他
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肺炎、白血病和包括流感在内的其他疾病的文章。
亨里克是最早向神水和民间偏方发起 挑战的人之一,这些东西确
实让流感病人受到了伤害,甚至因此而丧命。亨里克经历了两次流感大
流行,分别是1890年和1918年。他的诉求很简单
[39]
:在没有证据表明
它们会起作用之前,医生们不能把能用的药都用上。
在1919年夏天写下这篇文章需要很大的勇气,当时美国和世界其他
地区正从史上最严重的流感大流行中恢复过来。亨里克写道,“大多数
治疗流感的医生都是基于‘肤浅的观察和有限的经验’而进行治疗的。他
们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疾病是有自限性的,即它常常能够自愈。”
“所以许多结论都是很粗糙的,”亨里克写道,“它们是通过臆想得
出的,在这个过程中,乐观的轻信取代了探索性的科学质疑。”
亨里克对各种粗制滥造的治疗方案持怀疑态度,这些疗法轻则会让病人神志不清,重则会致死。打一针水银?超高剂量的奎宁?“当
然,”他用一种特有的轻描淡写的语气写道,“有的人得出这些结论时犯
了错误。”
[40]
亨里克说:“让我们尝试一些更切合实际的真正有效的方法,而不
是开些毫无作用的药物。例如,隔离和戴口罩,以防止传染;让病人多
喝水,以防止脱水;还要多休息,要好好地休息。”几周的卧床休息,少量户外活动,多呼吸新鲜空气,保持安静,多睡觉。他的治疗方案恰
恰代表了保守派的主流意见
[41]。
当然,亨里克也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所以我们也不必惊讶于他也
赞成使用泻药
[42]
,并坚持“在患病初期肠道必须彻底打开,且在任何时
候都不可以让肠道失去活力”。我们应该对他的这个观点表示宽容和理
解,因为他发表了一些其他超越时代局限的常识性观点:
在治疗严重的自限性传染病时,最难做到的事情之一就是不要仅仅因为确诊了就
开药。当想到流感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时,头脑再冷静的医生的自我约束也会被置之
脑后。在流感肆虐的时候,带着一丝歇斯底里的恐慌气氛在人群中蔓延扩散,医生过
去形成的良好判断力也会变得找不着方向。医生会忘记其实大多数流感病人根本不需
要服用什么药物。本来就不该有什么常规治疗方案规定了某些药物应该在某个时间段
使用,而根本不考虑是否有一个清晰的用药指征。治疗方案应该给患者带来希望,根
据患者的症状来确定,因人而异。
最后一句是金句。这句话值得每所医学院的每位医学生牢记。等一
等,看一看会发生什么,针对病人的症状用药,看看病人的个人档案,考虑病人的情况,进行个性化治疗。
幸运的是,也有其他一些医生认为大多数的流感治疗都是不正确
的。1918年11月,一名驻扎在英格兰布兰肖特营地的加拿大随军医生写
道,对于大量用于流感治疗的药物而言
[43]
,“显而易见,它们大部分都
是徒劳无功的”。几千年以来的治疗方法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但从某种程度上说,病人并没有变化。毕竟病毒的类型是一样的,折磨
古希腊人的病毒,也是把不幸的灵魂送到霍普柯克医生面前的病毒,也
是把你的配偶、孩子或你自己打倒的病毒。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
当然,我的同事们至少不会给你开一剂泻药。我也不会让你去放
血。但当你得知这么多年来流感的治疗方案并没有多大的进步时,你或
许会感到惊讶。
下面是美国每年会发生3100万次以上的事件的 一个典型总结
[44]。
深秋时节的某个周五的晚上,你开始觉得不舒服。你感到疲惫,不想吃
东西。你的后背和大腿开始疼痛。然后你觉得一阵寒战,开始冒汗。你
量了下体温,102华氏度(约39摄氏度)。现在你真正开始感到难受
了。寒战变得更厉害了。你的喉咙开始觉得痒痒,继而是疼痛。你开始
打喷嚏。到了周六的早上,你开始流鼻涕、咳嗽,而且觉得全身酸疼。
你得了流感。
对于这一常见的场景,每个人的反应都有所不同。你可能会待在家
里,服用泰诺或布洛芬,把体温降下来,并缓解疼痛。你也可能躺在床
上,睡睡醒醒。如果你是个幸运儿,或许会有人来照顾你,给你端来一
杯热水或热饮料。过了两天,你终于不再发烧,体力也开始恢复。到了
周一,你只好请病假,但你终于可以拖着沉重的身子去浴室洗澡了。尽
管没有食欲,但你可以喝点汤。到了周二,烧退了,你的食欲也在慢慢
恢复。到了周三,你已经痊愈了,可以重回办公室了。
这是大多数健康人得了流感之后的表现。只是大多数,不是全部。
有些人在开始有发烧或身体疼痛的迹象时,会联系他们的初级保健医
生。医生会告诉他们待在家里多喝水,如果症状没有好转就去急救中心。到他的诊室去,是医生最后才会想让你做的事。这样你就会把病毒
传染给他、他的员工和其他的病人。我在急救中心诊治过数以百计的流
感病人,许多人还处在发病早期,甚至有些人的症状还不明显,而我能
做的就是让他们回家,并送上我妈妈常对我说的嘱咐:多喝鸡汤。
不过有些病人得了流感却会有生命危险。他们可能是老年人,或是
免疫系统受到艾滋病病毒、化疗、或甾体类药物损害的人。还有些人可
能免疫系统是健全的,但是不巧遇上了某种特定流感的大暴发。还有的
人可能平时饮水不足,或者是由于呕吐或腹泻导致脱水。这些都是流感
的重症病例,常常需要到急救中心来救治。他们大多数是开车或坐出租
车来的,还有些是救护车送来的。
不管是以何种方式来的,到了急救中心后 遇到的第一个人肯定是
分诊护士。她会快速询问病人的病史,然后测量他们的脉搏、血压和体
温,并把一根探头放在他们的指头上来检测血液中的氧气含量(血气
针)。如果这四项检测(汇总起来就是你的“生命指征”)高于或低于正
常值,就会被要求戴上口罩,坐在等候室,直到有空的床位。坐在那里
时可能会看到其他三三两两戴着口罩的病人,穿着睡衣,肩上披着宽大
衣服,也在候诊。已经虚弱到无法走路的病人会被优先安排进入急救中
心。
如果是特别严重的流感季,会有许多症状一样的病人挤满了等候
室。如果是在下午或傍晚到达,那是大多数急救中心的高峰时段,候诊
时间会相对较长。如果在城里的急救中心就诊,那么会比在郊区的急救
中心就诊花费更长的候诊时间。周五和周一常常是一周里最忙的时候,而联邦假期和清晨的几个小时常常是人最少的时段
[45]。联邦假期后的
第一天,急救中心常常极其忙碌。请记住,医务人员在换班时可能动作
最为缓慢
[46]。我把上述信息都放在一起,是为了告诉你,如果得了严
重的流感,需要去看急诊,那么最好是在圣诞节假期的早上7点。一旦有了床位,病人会被扎很多针,其中一根静脉针刺入血管,取
血样。这些都是在医生看 到病人之前完成的。当医生来了以后,他会
问病况:起始时间、症状,等等。医生这样问有两个目的:第一,排除
病人没有肺炎等需要注射抗生素或住院的严重疾病;第二,想要弄清楚
是否需要其他的干预措施,比如额外的静脉输液。如果病人确实患了流
感,而且不需要静脉输液,那么只需要一些泰诺(在美国是一笔相当昂
贵的医药费账单)就可以回家了。
那么,医生是如何知道病人是否感染了流感呢?我不得不承认,即
使经历了5年的医学院教育、4年的住院医师培训和几千个小时的看诊,我们在急救中心的大多数医生也只是凭直觉判断。当然我们会问些重要
的问题来排除某些疾病,比如“你近期去过非洲吗?”或者“你是否曾接
触过一氧化碳?”最后一个问题很重要。如果病人没有因为一氧化碳中
毒身亡,那么一氧化碳会引起酷似流感的症状。流感高发期是在秋冬两
季——此时人们会用加热器和火炉,一氧化碳中毒常常被误诊为流感。
几年前,一起医疗事故索赔诉讼中,我作为专家见证人出庭作证。
在这个案子里,丈夫、妻子和儿子被发现死于他们费城的家中,死因是
一氧化碳中毒。后来发现,这位妻子曾去当地的急救中心就诊,症状是
头痛、恶心和呕吐。她去了两次。但是医生两次都没有考虑到一氧化碳
中毒的可能,相反,她的症状被认为是流感引起的。陪审团最后裁定被
告支付近190万美元赔偿款
[47]。
一旦确诊为流感,医生们就开始讨论治疗方法。如果有发烧,医生
会建议服用退烧药。这是每个急诊科医生都会做的事,也包括我。但事
实上,我们最好问问是否真的应该把烧退下来。
对于几乎所有人而言,发热从任何角度考虑都 不是危险的。但它
们让人难受,所以我们要去对付它们
[48]。有证据表明,发热其实是有
益的。原因很简单:当身体发热时,免疫系统能够更好地抵抗感染。当白细胞大量从骨髓中释放出来时,它们能够更好地和感染作战。发热还
可以增强另外一群叫自然杀伤细胞(NK细胞)的血细胞的活力
[49]
,提
升巨噬细胞(macrophages,希腊语里是“大胃王”的意思)吞噬和摧毁入
侵细胞的能力。
当体温略微升高时,身体能够更好地与感染做斗争,那么如果退烧
之后是否会给病人带来更糟糕的后果呢?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一个
研究小组对一组人进行了观察,他们想看看那些服用了退烧药物的流感
病人会发生什么。一旦他们觉得身体好些了,流感病人们就会下床,参
加社交,同时也开始传播病毒。从整个人口层面看,影响相当大。麦克
马斯特小组认为,频繁用药物干预发热的操作会将流感的传播性增强至
少1%。我知道这听起来也没什么,但是可别忘了美国每年死于流感的
人数高达4.9万
[50]。如果你把麦克马斯特小组的预估代入这些流感数字
中
[51]
,美国每年差不多有500人(或许其他地方有更多人)可以通过在
流感治疗中避免使用退烧药而被救回来。
在急救中心,我也总是会给发热的流感病人开药。而且,据我所
知,每个急诊科医生都会这么做。一部分原因是我接受过职业培训,另
一部分原因是发热真的让人难受。同时,这也是病人所希望的。人们希
望发热能够被治疗。此时向一个渴望浑身疼痛得到缓解的病人去解释麦
克马斯特的研究论文就显得费时费力了。
我常常给流感病人提供的另一种 治疗方法是静脉输液。对于有脱
水症状的病人,这非常重要。经过一两袋含有无菌水、盐和一些电解质
的静脉输液后,病人常常感到明显好转。我见过无数流感病人被救护车
送到急救中心,虚弱到无法站立。1小时后,输了两袋流体,他们就能
够走出急救中心自行回家了
[52]。
验血通常不是必要的,胸部X光检查也只会让病人受到不必要的辐
射。有的病人可能来到急救中心时流感症状没那么重,却希望医生能够给他做血液和X射线检测。事实上,没有必要将这些检查视作一理所当
然的常规操作。把这个决定权交给医生,不要自己主动提出来要做血检
或X射线。这些检查除了增加你账单上的数字,毫无用处。我几乎从不
开这类检查,但也有例外。一些病人看起来非常虚弱,极度脱水,或者
合并其他慢性病。还有些人可能是老烟鬼,还有些人可能已经得了肺
炎。他们可能会窒息。当我借助于听诊器听他们的肺音时,能听到噼啪
声和喘气声(或者叫“罗音”[rales]和“干罗音”[rhonchi])。对这些
病人来说,肺部X光片是必须要做的,因为通过片子可以判断是否得了
肺炎。血液检测将会发现有大量的白细胞,提示有一系列感染。我能够
给予这些病人的首要治疗步骤就是让他们吸纯氧。在我们的肺里有成千
上万个小囊泡,叫肺泡,氧气通过肺泡进入我们的血流。在被流感和肺
炎破坏的肺中,这些肺泡充溢着体液和脓液,进入血液的氧气有所减
少,导致呼吸短促急迫。含氧量高的血液颜色是鲜红的,没有氧气的血
液颜色是暗红的。当氧气水平变得相当低时,嘴唇和耳朵会变得暗沉。
这被称为紫绀,是病人病情严重的信号。这也是1918年流感大流行时重
症病例的共同特点之一。吸氧可以用来治疗紫绀或低血氧症,并在几分
钟之内就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
这些病重的患者必须住院,接受抗生素治疗以对抗肺部的细菌感
染。他们还需要输液,以保持他们身体水分充足,需要继续保持吸纯
氧。大多数人只需要在病房里待几天病情就可以改善,但如果肺部受损
严重、扩散范围持续扩大,就需要转移到重症监护病房。在那里,每个
病人都有专门的护士看护,病情的每个变化都需要密切监视。如果病情
恶化,需要使用镇静剂,同时连接上一个可以代替他们呼吸的机器。一
根大约9英寸长、食指粗细的管子通过喉咙沿着气管滑进去。一端连着
呼吸机,每循环一次,病人的胸部就会扩张收缩一次。然后我们能做的
就是等待了。
如果一切顺利,肺炎会缓解,流感引起的炎症也会慢慢消退。几天后就可以撤去呼吸管,镇静剂的用量也会慢慢减少。病人慢慢苏醒,对
刚刚进行的激烈的生死之战一无所知。这是一切顺利的结果。但有时候
肺炎太严重以至于病情无法得到有效控制。首先肺功能会衰竭,然后是
肾和肝等多个器官衰竭。最后,流感又将夺去一个生命。
我这么说并非出于一种病态。在每年感染流感的数百万人中,只有
不到1%的人会死亡。对于来到急救中心的人来说,大多数人只是需要
被医生再次告知“时间”是治愈流感所需要的一切。现在最大的误区之一
是不管大小病都需要抗生素。如果一个健康人得了普通流感,不需要抗
生素,医生也不该开抗生素类的药物。抗生素对病毒没用,所以它们对
治疗流感也一点儿用都没有。然而如果有并发症且病毒性流感发展成了
细菌性肺炎,此时当然应该用抗生素。但是,我要重复一遍的是,抗生
素对流感病毒没用。你也许会惊讶,竟然有这么多的患者明知是病毒感
染还是会要求医生开抗生素。当我拒绝了他们的要求时,他们会失望不
满。医生需要对这个问题负主要责任。有可信的数据显示,有大约一半
病毒感染患者(如“流感”)拿到了完全没用的抗生素
[53]。
简直无法想象,我们曾经将放血、灌肠、香槟、毒气、蓖麻油视作
治疗流感最先进的方法。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我们经历了漫长的探索。尽
管现代医学显示出了种种优越性,但治愈流感仍然是我们未解决的难
题。我们仍然受到流感病毒的威胁,担心1918年流感大流行会卷土重
来。要想知道为什么流感依然难以治愈,我们需要深入了解病毒本身。
[1] K. Saketkhoo,A. Januszkiewicz,and M. A.Sackner,“Effects of Drinking Hot Water,Cold Water,and Chicken Soup on Nasal Mucus Velocity and Nasal Airflow Resistance”,Chest 74,no.4 (1978):408-10.
[2] B. O. Rennard et al.,“Chicken Soup Inhibits Neutrophil Chemotaxis In Vitro”,Chest 118
no.4 (2000):1150-57.
[3] “Chicken Soup for a Cold”.2017年12月10日登录,https:www.unmc.edupublicrelationsmediapress-kitschicken-soup.[4] D. M. Morens,“Death of a President”,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41,no.24
(1999):1845-49.
[5] Mary Thompson,“Death Defied”,George Washington’s Mount Vernon.2017年11月11日登
录,http:www.mountvernon.orggeorge-washingtonthe-man-the-mythdeath-defied-dr-thorntons-
radical-idea-of-bringing-george-washingtonback-to-life.
[6] 盖伦,即克劳迪亚斯·盖伦(Claudius Galenus,129-199),是古罗马时期颇具影响力的
著名医学大师,他被认为是仅次于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医学权威。盖伦是著名的医
生、动物解剖学家和哲学家。他一生专心致力于医疗实践解剖研究、写作和各类学术活动,撰
写了五百多部医学著作,并根据古希腊体液说提出了人格类型的概念,主要作品有《气质》
《本能》《关于自然科学的三篇论文》。——译者注
[7] J. A. B. Hammond,W. Rolland,and T. H. G. Shore,“PurulentBronchitis:A Study of
Cases Occurring amongst the British Troops ata Base in France”,Lancet 190,no.4898 (1917):
41-45.
[8] C. E. Cooper Cole,“Preliminary Report on InfluenzaEpidemic at Bramshott in September-
October,1918”,British Medical Journal 2,no.3021 (1918):566-68. “In some cases
venesection relievedthe toxemia,especially if ombined with (1)saline or (2)glucose and
salineinterstitially,intravenously,or by the rectum.”
[9] Heinrich Stern,Theory and Practice of Bloodletting (NewYork:Rebman Company,1915),iv.
[10] W. F. Petersen and S. A. Levinson,“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Venesection with Reference
to Lobar Pneumonia”,JAMA 78,no.4 (1922):257-58. 彼得森(Petersen)和列文森
(Levinson)是真正支持放血疗法的人。“我们相信放血疗法,并想向许多年长的有能力的临床
医生强调,静脉放血术有时可带来显著的疗效,这种疗效具有明确且合理的基础。”
[11] 但是这仍然经历了较长时间。在G.B.Risse的文章里,作者讨论了它是如何退出历史舞
台的:“The Renaissance of Bloodletting:A Chapter in Modern Therapeutics”,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and Allied Sciences 34,no.1 (1979):3-22.
[12] A. F. Hopkirk,Influenza:Its History,Nature,Cause and Treatment (New York:The
Walter Scott Publishing Company,1914),155. 在这里我可能太苛刻了,因为几乎所有医生在
治病时(不管是何种临床症状)都会用同样的方法,即泻药和催吐药。见David Wootton,Bad
Medicine:Doctors Doing Harm Since Hippocrate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13] 1917年2月,阿司匹林生产厂商拜耳失去了该药物的专利,其他生产企业可以生产该药
物并涌入市场,使得人们在不管是何种治疗方案下都能够很容易获得大剂量的阿司匹林。1918
年9月,美国卫生局局长表示,阿司匹林已经在国外成功用于缓解各类疾病症状。在随后的一个月内,流感死亡人数达到峰值。
[14] Richard Collier,The Plague of the Spanish Lady:The Influenza Pandemic of 1918-1919
(London:Macmillan,1974),106.
[15] 格令,是历史上使用过的一种重量单位,1格令等于0.0648克,一般用于称量药物等。
——译者注
[16] 参见K. M. Starko,“Salicylates and Pandemic Influenza Mortality,1918-1919
Pharmacology,Pathology,and Historic Evidence”,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 49,no.9
(2009):1405-10. 另参见JohnM. Barry,The Great Influenza:The Epic Story of the Deadliest
Plague in History (New York:Penguin,2005),353,358.
[17] Hopkirk,Influenza ,159.
[18] 品脱,容量单位,英制1品脱等于0.5683升。——译者注
[19] Hopkrik,Influenza ,156.
[20] D. C. Smith,“Quinine and Fever:The Development of the Effective Dosage”,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s 31,no.3 (1976):343-67.
[2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Guidelines for the Treatment of Malaria”,Geneva,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15.
[22] Smith,“Quinine and Fever.”
[23] Cooper Cole,“Preliminary Report on Influenza Epidemic at Bramshott.”
[24] H. A. Klein,“The Treatment of ‘Spanish Influenza’”,JAMA 71,no.18 (1918):1510.
[25] “...iletaitlogique d’avoirrecours aux injectionspour traitercette infection comme on le fait pour
le paludisme.”参见F. Fabier,“Traitement de la Grippe par les Injections de Quinine”,Journal de
Médecine et de Chirurgie Pratiques 90 (1919):783-84,另参见M. L.Hildreth,“The Influenza
Epidemic of 1918-1919 in France:Contemporary Concepts of Aetiology,Therapy,and
Prevention,”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4,no.2 (1991):277-94 .
[26] 参见Muskogee Times-Democrat ,December 1,1919,6.
[27] M. E. Boland,S. M. Roper,and J. A. Henry,“Complications of Quinine
Poisoning”,Lancet 1,no.8425 (1985):384-85.
[28] Hopkirk,Influenza ,163,180.[29] Hopkirk,Influenza ,167.
[30] “Influenza:Its History,Nature,Cause and Treatment”,book review,JAMA 63,no.3
(1914):267.我仍然无法确信评论员蔑视的是谁,英国人还是霍普柯克医生?我喜欢“万灵
药”(nostrum)这个词,它意味着一种由不合格的人制备的无效的药物。
[31] R. J. Sherertz and H. J. Sherertz,“Influenza in the Preantibiotic Era”,Infectious Diseases in
Clinical Practice 14,no.3 (2006):127.
[32] Roger Welsch,A Treasury of Nebraska Pioneer Folklore (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67),370.
[33] “Influenza Discussions”,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no.2 (1919):136.
[34] A. Gregor,“A Note on the Epidemiology of Influenza among Workers”,British Medical
Journal 1,no.3035 (1919):242-43.
[35] F. Shufflebotham,“Influenza among Poison Gas Workers”,British Medical Journal 1,no.3042 (1919):478-79. 由于某些原因,这种免疫并未延展到光子气工人身上。光子气在第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产生了非常恐怖的效果。
[36] E. W. Rice et al.,“Chlorine Inactivationof Highly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 Virus
(H5N1)”,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13,no.10 (2007):1568-70.
[37] “James B. Herrick (1861-1954)”,JAMA 16,no.186(1963):722-23.
[38] 参见C. S. Roberts,“Herrick and Heart Disease”,in H. Kenneth Walker,W. Dallas Hall,and J. Willis Hurst,eds.,Clinical Methods:The History,Physical,and Laboratory Examinations
,3rd ed. (Atlanta:Butterworth Publishers,1990). 另参见R. S. Ross,“A Parlous State of Storm
and Stress. The Life and Times of James B. Herrick”,Circulation 67,no.5 (1983):955-59.
[39] James B. Herrick,“Treatment of Influenza by Means Other Than Vaccines and
Serums”,JAMA 73,no. 7 (1919):482-87.
[40] 所有这些引言都是来自亨里克,483.
[41] “Proceedings of the Forty-Six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no.2 (1919):130-42.
[42] 这段引言来自亨里克,483. 这种对流感病人的肠蠕动的关注获得了非常广泛的传播,并成为医学根深蒂固的知识。这里是一封医生的信件的节选,于1918年11月发表在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我不能过于强调使用温和的泻药使肠道畅通的重要性,但常
见的情况是,在肠道的一次快速导泻之后,高烧会缓慢消退,这种方法对于缩短流感的病程非常有帮助。”来自Klein,“The Treatment of ‘Spanish Influenza’”,1510.
[43] Cooper Cole,“Preliminary Report on Influenza Epidemic at Bramshott”.
[44] N. A. Molinari et al.,“The AnnualI mpact of Seasonal Influenza in the U.S.:Measuring
Disease Burden and Costs”,Vaccine 25,no.27 (2007):5086-96.
[45] 这些观察是基于我自己25年来在美国和国外多个急救中心的工作经历。幸运的是,我
的经历似乎和已发表的数据高度匹配。我的前同事梅丽莎·麦卡锡(Melissa McCarthy)对一个
大型的市区教学医院急救中心接收病人的时间点持续了超过一年的研究。她发现,周一和周五
最忙,并且早上较早的几个小时是最悠闲的。See M. L.McCarthy et al.,“The Challenge of
Predicting Demand for Emergency Department Services”,Academic Emergency Medicine 15,no.4
(2008):337-46.另见S. J. Welch,S. S. Jones,and T. Allen,“Mapping the 24-Hour Emergency
Department Cycle to Improve Patient Flow”,Joint Commission Journalon Quality and Patient Safety
33,no.5 (2007):247-55. 这些模式在全世界的急救机构中都有被发现,如Y. Tiwari,S.
Goel,A. Singh,“Arrival Time Pattern and Waiting Time Distribution of Patients in the Emergency
Outpatient Department of a Tertiary Level Health Care Institution of North India”,Journal of
Emergencies,Trauma,and Shock 7,no.3 (2014):160-65.
[46] 大多数急救室是三班倒:早上7点到下午3点、下午3点到晚上11点、晚上11点到第二天
7点。此外,对于一家特定的急救室而言,会有许多额外的班次的重叠组合,这取决于病人达到
高峰的时间。
[47] A. Elliott-Engel,“Jury Awards 1.87 Million in CarbonMonoxide Poisoning Case”,Legal
Intelligencer ,June 1,2011.
[48] 参见M. Glatstein and D. Scolnik,“Fever:To Treat or Not to Treat?” World Journal of
Pediatrics 4,no.4 (2008):245-47. Adated but useful review of the subject is Matthew J. Kluger,Fever:Its Biology,Evolution,and Function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
[49] 有一项关于发烧和免疫热调节的综述写道:“发烧所带来的体温升高是一种全身报警系
统,它可以在外来病原体入侵时广泛地激发免疫监视。”参见 S. S. Evans,E. A. Repasky,and
D. T. Fisher,“Fever and the Thermal Regulation of Immunity:The Immune System Feels the
Heat”,National Review of Immunology 15,no.6 (2015):335-49.
[50] 这是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估计,参见“Estimating Seasonal Influenza-Related
Deaths in the United States”.
[51] D. J. Earn,P. W. Andrews,and B. M. Bolker,“Population-Level Effects of Suppressing
Fever”,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Biological Sciences 281,no.1778 (2014):
20132570.[52] 静脉输液是一种简单的介入治疗方式。生产厂家对一袋输液的定价只有1美元,但是医
院往往会有较高的加成。《纽约时报》有个调查显示,有些人被要价787美元用于支付“输液治
疗”。还有一个例子,一个病人被要求花费91美元来支付一个医院采购成本仅有0.86美元的输
液。你可以把酒店的迷你吧当成某种意义上的敲诈。参见Nina Bernstein,“How to Charge 546
for Six Liters of Saltwater”,New York Times ,August 27,2013.
[53] C. G. Grijalva,J. P. Nuorti,and M. R. Griffin,“Antibiotic Prescription Rates for Acute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s in U.S. Ambulatory Settings”,JAMA 302,no. 7 (2009):758-66.2 流感:病毒的前世今生
病毒早在人类诞生之前就已存在。病毒诞生的时间比智慧生命、类
人猿、黑猩猩、爬行动物以及任何从黏液中孕育的生命诞生的时间都要
久远。病毒无处不在,天生神秘。我们并不知道病毒是如何演变发展
的,但我们知道它们已经存在了数百万年。病毒存在于生命的边缘
[1]
,挑战我们对生物的认知。石头没有生命,但是细菌有,病毒则介于两者
之间。
病毒是一系列不具备基本细胞结构的化学物质组成的盒子。病毒不
能自行代谢或再生。为了繁殖,它必须入侵活体细胞。病毒能够感染细
菌、植物、爬行动物、鱼类、鸟类以及哺乳动物。病毒与人类的进化密
不可分。几千年来,部分病毒已与人类的遗传密码合为一体
[2]。隐蔽于
人类DNA长链中的序列就源自古代的病毒。他们的遗传密码与我们的遗
传密码息息相关,病毒由此成为人体无害的一部分。病毒的繁衍完全依
靠人体细胞来获取营养。
————
“virus”(病毒)一词在人类发现病毒颗粒 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这是
一个拉丁词语
[3]
,意思是“毒药”“毒液”或“有害气味”。中世纪,“病
毒”与“毒素”同义。在拉丁文医学文本的英文版本中,这个词仍未经过
翻译。到了18世纪,病毒一词可以用来指代任何传染病。例如,爱德华
·詹纳(Edward Jenner)
[4]
在发现预防天花的疫苗之前,就用这个词来
描述天花产生的原因。在19世纪,伴随着疾病细菌理论的迅速发展,“病毒”一词依然被用来表示致病因子,或有无细菌感染。路易·帕
斯特(Louis Pasteur)将引起狂犬病的致病因子称之为“levirus rabique”
[5]。如今,我们知道病毒属于亚微观实体,其体积比细菌还要小20倍。病
毒的核心部分是遗传物质
[6]
,外面覆盖着蛋白质外壳,它们仅能在活体
细胞内繁殖。
正如“病毒”一词在具备如今的意义之前就已经被人们使用了很久一
样,“流感”一词诞生的时间也比目前人们使用的时间要久远。没有人能
够确定英文词语“influenza”最初是否用来描述目前被人们称之为“流
感”的这种疾病,但早在1504年,这个词语就出现了。该词来自意大利
语,意思是“影响”(influence)。这就说明它源自占星理论。人类曾经
认为流感是由恒星和行星的错位造成的。
直到20世纪,我们才确切地知道病毒到底是什么。在此之前的数千
年间,人类一直为这种看不见的力量所困扰,并为此做了种种假设。撰
写了爆发于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古希腊历史学家修
昔底德(Thucydides),记录了公元前430年发生的一场长达3年的瘟疫
[7]。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雅典寻求庇护。这座城市很快就人满为患。这
就为传染病的暴发创造了最佳条件。修昔底德描述这种疾病最初的症状
是“头部发热和眼睛发红”,之后出现打喷嚏以及声音嘶哑症状,“不久
后,这些症状演变为胸腔剧烈的 咳嗽”。高烧严重时,患者们不得不跳
入蓄水池为自己降温,而且他们还会通过喝酒来缓解持续的口渴。修昔
底德对患者的存活时间感到诧异,然而,大多患者在一周内就殒命了。
驻扎在雅典的1.3万名士兵中有三分之一的人被这场流行病夺去了生
命。然后,奇怪的是,在公元前427年的冬天,这场流行病出乎意料地
结束了。
长期以来,这种疾病一直被视为历史谜团。有人怀疑是瘟疫和斑疹
伤寒,但也有人说是炭疽、伤寒和肺结核。这种疾病发病快、潜伏期短。那些生病之后得以康复的人——包括修昔底德本人——并没有再患
这种病。这种疾病一波接一波来袭,常见于人口聚集的地方。20世纪80
年代,研究人员将这组病症称为“修昔底德综合征”。研究人员还注意
到,这种疾病的症状具有流感大流行的特征,同时伴有继发细菌性感
染。疾病的暴发与1918年的流感疫情有诸多共同特征,包括造成多人死
亡的继发感染。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修昔底德综合征就是有关流感
的最早记录。由于死亡率极高,所以这种流感也极具致命性。
在修昔底德之后的100年里,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描写了一种听起
来像流感的疾病
[8]
,这种疾病每年暴发一次。这种疾病的外观与在北半
球的秋冬季可见的昴宿星团(the Pleiades,又称“七姐妹星团”)相似。
在这段时间里,希波克拉底写道,“许多人持续不断地发烧”,病人发
冷,经常出汗,并伴有咳嗽。
之后,直至中世纪晚期才有流感暴发的相关记录,此时天花和鼠疫
是最令人恐惧的致命疾病。与这些大规模致命疾病相比,流感的影响力
几乎难以察觉。
几个世纪后的1675年11月,我的家乡伦敦暴 发了一场流感
[9]。每
周的死亡人数从月初的42人增加到月中的130人,而在12月的第一周只
有7人死亡。除了致人死亡之外,这种疾病还有其他麻烦的特征。教堂
里的教徒们咳嗽得太厉害,以至于听不到牧师布道
[10]。有点讽刺意味
的是,英格兰北部的人们称这种疾病是“快乐的咆哮”(jolly rant,现在
该词专指流感患者),因为它将受害者变成了悲惨的噪声制造者。当
然,这并不是什么令人快乐的事。17世纪英国著名的医生托马斯·西德
纳姆(Thomas Sydenham)认为
[11]
,这些流行病与暴雨有关,是暴雨使
人们的血液中布满了“粗糙的含水颗粒”。放血疗法和泻药
[12]
被认为是
最佳的治疗方法。
————为了区分一般流行病和大流行性疾病,我们暂且不讨论血液和排便
这类话题。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些词语都在交替地用来描述流感的
暴发。2009年暴发的流感被称为猪流感。这恰恰是混淆两个术语的典型
例子。《纽约时报》上的一则标题就是“这是大流行性疾病吗?对‘大流
行性疾病’的定义”
[13]。虽然两者的范围和强度有区别,但没有人真正
认可它们的确切含义。我们目前最常用的定义是
[14]
一般流行病是一种
在地方暴发的严重疾病,而大流行性疾病是一种在全球暴发、从源头快
速传播的致人重病的疾病。按这个标准来看,17~19世纪中,每个世纪
都分别出现了3~5次流感大流行。其间一些流感大流行
[15]
暴发的时间
间隔达半个世纪,而其他几次则在几年时间内相继暴发。流感如此令人
困惑的部分原因是:从一般流行病和大流行性疾病的角度来看,随着季
节的更替,小规模的这种疾病可以预测,但是大规模的则无法预测。例
如,1730年的流感后的第二年又暴发了一次流感。在几乎一个世纪之后
的1831年和1833年又连续暴 发了两次流感。流感活动规律如此深不可
测,因此需要很长时间去跟踪和识别。
暴发于19世纪的一场特殊的大流行性疾病与以往的不同,它使人类
在揭开这种疾病的神秘面纱方面向前迈进了一步。1889年冬季暴发的具
有毁灭性的疾病不仅是现代第一次流感大流行,而且也是第一次有且详
细记录在案的流感大流行。据此,人们可以对其传播和影响情况进行评
估。这是40多年来英国暴发的第一次流感大流行。鉴于这场疾病形势严
峻,一位名叫亨利·帕森斯(Henry Parsons)的医生将该病上报给了议会
[16]。帕森斯指出,这次暴发的疾病肯定是一场大流行性疾病,因为整
个欧洲都在饱受病痛的折磨。之后,这种疾病又传播到美国
[17]。1889
年12月,在纽约报告了首起病例。次年1月,波士顿、圣路易斯和新奥
尔良都有人染病死亡。在波士顿,40%的人患病。超过四分之一的工人
因为病情过于严重而无法工作。过度拥挤和致命的“污浊空气”对疾病传
播有巨大的影响。在这场大流行性疾病中,富人和穷人都深受影响,但
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人群密集或密闭场所,患病率会更高”。帕森斯不知所措。他无法提供预防流感的方法,因为还有一个重要
谜团没有解开:病因。这是人们的猜测。帕森斯向议会提交的报告表
明,大流行性疾病已经在俄罗斯暴发,正在向西蔓延。但这里含有多少
科学分析的成分,又有多少具有沙文主义的成分?甚至有传言说
[18]
,这种大流行性疾病是由从俄罗斯进口的燕麦传播到英国的。这些燕麦先
是被马吃掉,然后马将疾病传给了人。其他起源论包括腐烂的动物尸
体、地震、火山爆发以及从“地球的内部最深处”排放到空气中的“臭
气”。甚至有人认为大流行性疾病是由木星和土星共同引起的
[19]。
帕森斯提出了1889年流感大流行暴发的三个可能原因
[20]。第一个
原因是天气。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么多的病 例几乎同时出现在整个
欧洲和美国。可能的原因是空气质量很差。或许大气中携带一种能在空
中繁殖然后感染一些易感人群的有毒物质?帕森斯承认,他知道没有任
何药剂能够做到这一点。尽管他认为这可能是由“非生命的颗粒物”
[21]
引起的——这种对病毒实质的描述非常准确。
第二个原因是流感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家庭
成员之间经常互相感染,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很多情况下某个家庭成
员将疾病传染给了整个家庭。帕森斯获得了英国大型铁路系统工人的流
感数据。感染率较高的是职员
[22]
,尽管他们没有暴露在外面的空气
中,但是每天与许多人接触,而机车驾驶员感染率较低,他们基本上暴
露在公开场合,但与乘客是隔离开的。帕森斯确信
[23]
,人群接触是疾
病传播的罪魁祸首。
帕森斯的第三个原因是,在某种程度上,动物对疾病的传播也起了
一定的作用
[24]
——特别是马、宠物狗、猫和笼养鸟。帕森斯再一次得
出了正确的结论,这一点比其他人早了大约50年。
————在弄清楚什么是病毒之前,科学家已经对细菌有所了解。19世纪40
年代,几位欧洲科学家各自得出结论:发酵过程中必需的酵母菌是一种
生物活体。发酵过程不仅是一种化学过程,也是一种由微生物活动引起
的生物过程。法国人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研究了发酵依赖酵母
和其他肉眼无法看到的微生物的方式。“巴氏杀菌法”就以他的姓氏来命
名加热液体杀死细菌的过程。巴斯德出生于1822年,在将注意力转移到
法国北部边境里尔市(Lille)当地啤酒厂所面临的问题之前,他的研究
领域是化学。他表示,发酵不仅需要活酵母菌,还需要一种微生物,那
就是他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的细菌。
巴斯德的细菌发现从总体上改变了生物学特别是医学的面貌。至少
自亚里士多德时代,哲学家和科学家们就一直认为自然发生说
(spohtaneous generation)解释了任何数量的生物现象出现的原因。这
也解释了为什么蛆虫会出现在腐臭的肉上,为什么有些植物可以在没有
种子的情况下发芽,为什么真菌会在腐烂的水果上生长。但是在19世纪
50年代进行的一系列巧妙的实验中,巴斯德表示,如果一个物体被适当
消毒,就不会出现自然发生现象。到1877年,科学家们确定了细菌会导
致人们患传染性疾病。这些微生物很快就被命名了。炭疽病是由杆菌引
起的,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细菌。不久之后,科学家们发现了咽喉部感
染、肺炎、麻风病等疾病的病原体
[25]。人们能够识别越来越多的细
菌,这种现象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在人们的热情和渴望中,科学家
们认定微生物是导致许多疾病的元凶。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些细菌实际
上是入侵弱化宿主的次生病原体。它们与疾病有关,但却不是病源。这
恰恰是人们在确定流感病因时犯的第一个错误。
1892年,两名在柏林工作的微生物学家声称他们已经发现了导致流
感大流行的细菌。他们称这种新细菌为流感杆菌(bacillus influenza)。
其他人将这种流感杆菌以其中一位发现者——微生物学家理查德·法伊
弗(Richard Pfeiffer)的名字命名为法伊弗氏杆菌(Pfeiffer’sbacillus)。当然,他们错了。这些流感患者身上肯定有细菌的存在,但
却不是形成流感的原因。相反,它们是一种继发性病原体。该继发性病
原体会入侵人们的身体,而此时人们的免疫系统已被我们现在所知的流
感病毒所击溃。细菌引起的流感并不比盘旋的秃鹰 杀死的鹿多,因为
狼才是鹿的主要死因。1918年,美国暴发了一场流感大流行。历史学家
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将法伊弗氏杆菌描述为“一个指
向错误的权威路标”
[26]。
今天,流感杆菌有了另外一个名称:流感嗜血杆菌(haemophilus
influenzae)。我曾多次为病人开抗生素来治疗这种令人讨厌的细菌,但
不明白为什么它的名字中含有“流感”这个词。它是肺炎、脑膜炎、耳部
感染以及更多疾病的元凶,但绝不是流感形成的原因。当我对流感相关
的混乱历史有所了解之后,其用词的不合理性就能说通了。这个名字来
自一个世纪前,而事实证明当时人们对流感的认知是错误的。
————
现在我们已经发现了这种病毒,但它具体是什么样子呢?是什么引
起普通感冒,让人多痰、流涕,为什么有的会变异成具有致命性的埃博
拉病毒?病毒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传播并折磨患者的呢?
进化,使病毒有别于我们体内发现的细胞。细胞含有微小的特殊器
官,而病毒没有类似的东西。由于缺乏线粒体,所以病毒无法制造能
量。病毒不含核糖体,所以它们不能构建蛋白质。病毒也缺乏输送废物
和毒素的溶酶体。这种病毒只是一个包含一束基因的框架,这束基因仅
仅是为了复制它们自身而存在。虽然计算机病毒的设计目的是为了让电
脑中毒并削弱或损害其功能,但大自然的病毒却并没有杀死细胞这个明
确目的。相反,它们唯一的目的是劫持一个细胞并把它当成一台复印机
来使用。为了做到这一点,病毒可能会伤害或破坏宿主细胞,但这只是
附带损害,而不是它们的首要目标。事实上,那些非常致命的病毒,可以在复制病毒之前杀死宿主细胞。流感病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和埃博拉病毒的致命 程度不同,但这些病毒采用的策略却是相
同的。它们入侵我们的细胞进行复制,然后必须寻找新的受害者来入
侵。病毒可能会让它们的宿主身体虚弱甚至死亡,但这是附带发生的。
我们现在已经认识了2000多种病毒,而且这个数量还在不断上升。
大多数医生只熟悉其中一些病毒。有一种疱疹病毒会致人患水痘(疱
疹)。而轮状病毒会引起幼儿腹泻。大约有100种不同的鼻病毒,这类
病毒会致使人们患普通感冒。还有像艾滋病病毒这样会导致人们患艾滋
病的逆转录病毒(retroviruses)。我们尤其对正黏液病毒
(orthomyxoviruses)这个有着笨拙名字的病毒家族感兴趣。“Ortho”一
词在希腊语中是“直的”的意思,而“myxa”的意思是“黏液”。正黏液病毒
家族包括流感病毒。实际上,有3种流感病毒株——分别为A、B和C,只有病毒株A和B能明显致人患病,而导致流感大流行的则是病毒株A。
流感是一种简单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病毒
[27]。它的形状像一个空心
球,内含8个病毒基因,由控制病毒功能的RNA(代替DNA)组成。
伸向外围的是两种重要的蛋白质,形状看起来像小小的穗状花序或
干草叉。尖尖的蛋白质被称为血凝素(hemagglutinin),或简称为
HA。在病毒被吸入肺部后,HA就会附着在细胞表面,这时,病毒的一
只脚已经迈入门内。细胞被诱骗,开始吸收病毒。一旦进入细胞,病毒
的包膜就会溶解并释放出8个基因,进入被入侵细胞的细胞核内。在那
里,它们强占了正常的细胞组织,并指导细胞制造数百万份的病毒颗
粒。然后,这些早期的颗粒回升到细胞膜内,就像沸腾的锅中的气泡一
样。由于被拴在表面,所以它们必须尽快摆脱束缚以入侵其他细胞。这
时,位于流感病毒表面上的第二个干草叉状蛋白质,被称为神经氨酸酶
(neuraminiolase)或NA,开始介入,并破坏细胞表面和病毒表面之间
的纽带。复制的病毒现在可以以 咳嗽或打喷嚏的方式自由地入侵另一名受害者。整个过程只需要几个小时,这些病毒就会离开被破坏的呼吸
细胞。那正是流感症状开始的时候。
在复制过程中,流感病毒可能采用两种方式之一发生改变,并且由
于这些变化,又产生了新的病毒株。如果构建新病毒的指令中存在复制
错误,第一种情况就会发生。这些指令被存储在8个病毒基因上,由遗
传密码构筑而成。当病毒复制时,该代码被读取并被复制数百万次。但
复制过程并不理想,因为其间会发生阅读或复制错误。因此,后代病毒
中的代码可能与亲代病毒的代码有所不同。遗传指令中的这些差异,导
致病毒表面的蛋白质发生了细微的变化。由于人类的免疫系统学会了通
过其表面上的蛋白质来识别流感病毒,因此这些细微的变化会导致免疫
系统无法识别流感病毒。这就是新病毒的发展方式,以及我们可能多次
感染流感的原因。从本质上讲,我们每次都会感染新的病毒。
要了解新病毒可能产生的第二种方式,我们必须明白甲型流感不仅
存在于人类身上,也会感染许多不同的物种,比如猪、鸟和马。有时,两种或更多种不同的病毒株会入侵同一肺部细胞。在那里,来自各个病
毒株的基因混合在一起并产生了一种杂交病毒,该杂交病毒含有来自双
亲的遗传物质。哺乳动物的肺部会感染流感病毒,而鸟类身上的病毒则
存在于肠道中。受感染的鸟粪可能含有数十亿的禽流感病毒,每种病毒
都可以与其他流感病毒株的遗传物质混合在一起,包括那些感染人类的
病毒的遗传物质。如果禽流感病毒和哺乳动物的流感病毒同时入侵一个
细胞,它们的基因就会混合在一起,从而产生一种全新的流感病毒。这
种新的流感病毒具有致命的杀伤力。这是1918年发生的事情,当时,鸟
类对这场流感大流行的生成、传播起到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1997年
在香港也发生过类似事件。一种新的禽流感病毒感染了与鸡有密切接触
的人。18名禽流感确诊患者中有6人死亡。只有那些直接接触鸟类的人
才会感染这种禽流感病毒,它在人与人之间并不相互传播。但只需要一
个小小的突变,病毒即可获得这种能力,从而为新的流感大流行做好准备。
虽然一个流感病毒就可以入侵细胞并繁衍数百万个后代,但实际上
只有为数不多的病毒具有繁殖能力。几乎所有发生的遗传变化都会损坏
病毒颗粒,致使其丧失繁殖能力。但鉴于感染流感后会产生数百万个病
毒颗粒,即使是成功率只有1%或2%,也会导致细胞中产生成千上万的
新型流感病毒并感染其他患者。
人类的免疫系统不断进化,已经可以预防和控制病毒、细菌和其他
外来病原体可能带来的感染。第一道防线由吞噬细胞(phagocytes)组
成,其名称来源于希腊语的意思“吞噬细胞”(devouring cell)。吞噬细
胞有点类似交警。它们总是在巡逻、侦察,发现、包围病原体,并将病
原体拉入细胞内,把它们消灭掉。吞噬细胞并不专门针对特定的细菌或
病毒。相反,吞噬细胞已经被编入人类的遗传密码中,以识别一般的病
原体。人类生来就具有这种先天性的免疫力,并且吞噬细胞无须事先接
触病原体就能够搜索、识别并破坏它。
人类免疫系统的第二道防线是抗原递呈细胞(antigen-presenting
cell)。这类细胞以特定的病毒或细菌为攻击对象。它们就像侦探,可
以描绘嫌犯的外貌。它们消化病原体并将其一些基本构成要素——例如
蛋白质或受体——呈现给另一种被称为辅助T细胞(helper T cell)的免
疫细胞。然后,这些T细胞大量增殖,并根据病原体的特征来确定相应
的敌人。与病原体首次相遇之后许多年,T细胞依然会记住它们的宿敌
并采取行动。这就是我们大多数人只患一次水痘的原因。我们与病毒的
第一次遭遇就会产生T细胞,这些细胞会永远保护我们。
人体始终会学着去抵御新的入侵者。疫苗接种就是利用了这一点。
通过向我们的免疫系统提供弱化的或无害的病原体,人体能够在感染疾
病之前制造抗体。免疫系统不在乎它是正常遭遇到病原体还是病原体通
过针头以疫苗的形式进入体内。无论哪种方式,免疫应答都是一样的。这样,下一次在身体遭遇病原体时,它能够更快更有效地对抗感染。如
果之前我们的免疫系统未能识别抗原,我们仍可能产生针对抗原的抗
体,但过程较缓慢。病情会越来越严重,持续时间也更长。在某些情况
下,如果无法对病毒立即发起攻击,可能会对人体产生致命影响。
流感会破坏人体精密的防御系统,因为它常常变换形态。流感经常
改变其表面的蛋白质,变得让人体难以识别。就像一个善于伪装的罪
犯,很容易就消失在人群中。这些变化为病毒提供了隐身衣,使得现有
抗体无法识别它们的存在。这就是你可能在某一季节中不止一次患流感
的原因:你的身体会产生针对第一种病毒的抗体,却会被它未能识别的
第二种病毒感染。这种“抗原漂移”(antigenic clrift)也是每年需要更新
流感疫苗的原因。病毒不断地变换外表,就像川剧“变脸”一样。
除了抗原漂移外,流感病毒还会经历更大的变化,即“抗原转
变”(antigenic shift),这正是人类患流感大流行的原因。在抗原转变期
间,病毒蛋白质呈现一种全新的结构。据说这种病毒很“新颖”。这些新
型病毒——通常在动物和人类病毒共享并交换它们的基因时出现——它
们就类似于新的罪犯,而不是伪装的老罪犯。所以这种新型病毒更狡
猾、更高产,也更致命。由于抗原转变,产生了致命的1918年流感病
毒,导致了2009年猪流感爆发。
通过漂移、转变、共享基因,流感的变形速度超过了人体识别它的
速度。在免疫系统开始产生针对一种病毒株抗体的过程中,不同的流感
病毒株会产生并演变成致命病毒。流感病毒的发展已经比我们的免疫防
御系统领先一步。
1918年的新病毒让数千万人丧命。关于这次流感流行病的第一份报
告来自欧洲。当年6月份的一份医疗报告很短,而且大部分内容含糊不
清,却对疫情暴发的位置进行了详细地描述:1918年5月28日,在西班牙的瓦伦西亚出现了一种性质不确定的疾病
[28]。这种疾
病的特点是患者发高烧,但是持续时间短,并且伴有类似于流行性感冒的症状。西班
牙的其他城市也发现了多例疑似病例。
接下来的一个月,在欧洲战事之外,《纽约时报》报道指出,一种
新的疾病——“西班牙流感”
[29]
,“在整个德国前线广泛传播”……这种
疾病妨碍了进攻战斗的准备工作。“无一人具有免疫力。在1个月之内,德皇本人也得了这种疾病
[30]。就像训练有素的军队一样,流感似乎有
自己的战术战略。但是这种战术战略极为隐秘。它不止一次袭击了所有
的战线。而第一批深受其害的人是士兵,他们曾经期望能参与一场别开
生面的战斗。”
[1] E. Rybicki,“The Classification of Organisms at the Edge of Life,or Problems with Virus
Systematics”,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Sciences 86 (1990):182-98.
[2] M. Emerman and H. S. Malik,“Paleovirology—Modern Consequences of Ancient
Viruses”,PLoS Biology 8,no.2 (2010):e1000301.
[3] Sally Smith Hughes,The Virus:A History of the Concept (London: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Science History Publications,1977),109-14.
[4] “……让牛痘病毒变得特别与众不同的是,一旦感染了牛痘的人在康复之后就不会再感
染了。”Edward Jenner,An Inquiry into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the Variolae Vaccinae,a Disease
Discovered in Some of the Western Counties of England,Particularly Gloucestershire,and Known
by the Name the Cow Pox (London:Sampson Low,1798),6. 我们在第九章里会再次提到詹纳
(Jenner).
[5] Hughes,The Virus ,112.
[6] Hughes,The Virus ,114.
[7] A. D. Langmuir et al.在以下文章中引用了这句话:“The Thucydides Syndrome. A New
Hypothesis for the Cause of the Plague of Athens”,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13,no.16
(1985):1027-30.
[8] Francis Adams,The Genuine Works of Hippocrates (New York:William Wood,1886),298.[9] Charles Creighton,A History of Epidemics in Britain ,2nd ed.,vol.2 (New York:Barnes
Noble,1965),328. 记录了咳嗽的更早期流行病学,就像发生在1658年4月的那场一样,然
而,流感常常是冬季特有的疾病,因此它也就不可能是4月咳嗽流行的原因。
[10] Charles Creighton,A History of Epidemics in Britain ,2nd ed.,vol.2 (New York:
Barnes Noble,1965),328.
[11] Charles Creighton,A History of Epidemics in Britain ,2nd ed.,vol.2 (New York:
Barnes Noble,1965),329.
[12] 1729年冬天的疫情流行起来特别粗暴,影响了英国、爱尔兰以及意大利。参见Charles
Creighton,A History of Epidemics in Britain ,2nd ed.,vol.2 (New York:Barnes Noble,1965),343页。不是所有大流行病都是流感。例如,在1743年4月有个流行病,当时“患者体温
升高时,皮肤常常发生红肿,随后,身体的大多数部位出现脱皮”,这不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病
毒性流感的描述,而更像曾经一度很常见的“猩红热”,是由链球菌感染所引起的。
[13] Lawrence Altman,“Is This a Pandemic?Define ‘Pandemic’”,New York Times ,June 8,2009,D1. See also D. M. Morens,G. K. Folkers,and A. S. Fauci,“What Is a
Pandemic?”,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 200,no. 7 (2009):1018-21.
[14] K. D. Patterson,Pandemic Influenza,1700-1900 (Totowa,NJ:Rowman and
Littlefield,1986),5.
[15] K. D. Patterson,Pandemic Influenza,1700-1900 (Totowa,NJ:Rowman and
Littlefield,1986),83.
[16] Henry Franklin Parsons,Report on the Influenza Epidemic of 1889-90 (London,Eyre and
Spottiswoode,1891).
[17] Henry Franklin Parsons,Report on the Influenza Epidemic of 1889-90 (London,Eyre and
Spottiswoode,1891),24-27.
[18] Henry Franklin Parsons,Report on the Influenza Epidemic of 1889-90 ,107页,在本书的
另外一处(第102页),帕森斯还引述了一个法国教授的观点:“流感是从俄国的土壤里滋生出
来的,而且这种疾病是悄无声息的,而非轰轰烈烈的。”帕森斯对这个说法表示怀疑。他指出,在俄国出现的情况和在欧洲其他地区出现的情况一样:“如果这种情况可以证明俄国有流感滋生
的土壤,那为何别处没有呢?”当我写这段话时,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正在调查俄罗斯对于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影响,这相当具有讽刺意味。还有没有什么事不会怪到俄罗斯头上的?
[19] Creighton,A History of Epidemics in Britain ,397-409.
[20] Parsons,Report on the Influenza Epidemic of 1889-90 ,70.[21] Parsons,Report on the Influenza Epidemic of 1889-90 ,82.
[22] Parsons,Report on the Influenza Epidemic of 1889-90 ,73.
[23] Parsons,Report on the Influenza Epidemic of 1889-90 ,102
[24] Parsons,Report on the Influenza Epidemic of 1889-90 ,106.
[25] Hughes,The Virus ,6-8.
[26] Alfred W. Crosby,America’s Forgotten Pandemic:The Influenza of 1918 ,2nd e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269.
[27] J. K. Taubenberger,A. H. Reid,and T. G. Fanning,“Capturing a Killer Flu
Virus”,Scientific American 292,no.1 (January 2005):62-71.
[28] “Undetermined Disease—Valencia”,Public Health Reports 33,no.26 (1918):1087.
[29] “Spanish Influenza Is Raging in the German Army”,New York Times,June 27,1918 .
[30] 在一句话的电讯中,该报纸称“德皇和皇后患有轻度西班牙流感”。“Kaiser Has
Influenza”,New York Times ,July 19,1918.3 来势汹汹: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
劳瑞·迈纳(Loring Miner)博士是美国堪萨斯州的一名乡村医生,他的医学实践完全不同于今天。他居住的地方离最近的医院也很远,在
当时难以想象会有现代的医学设备。尽管他所生活的时代存在技术局
限,但迈纳博士在1918年的流行病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18年,迈纳拥有了一间庞大的办公室。他在850平方英里的平坦
农田上进行乡村医学实践。这些农田由1720名潜在的患者进行种植和收
获。哈斯克尔(Haskell County)是堪萨斯州西南部的一块完整的土
地,位于威奇托(Wichita)以西200英里处。1918年1月和2月,农闲时
节,迈纳博士发现了数十例严重流感病例,他称之为“未确定性质的病
症”。仅在一天内,就有18人患病,并有3人死亡。在像哈斯克尔这样人
烟稀少的地方,这种现象是如此引人注目以至于迈纳博士给卫生官员写
了一份报告
[1]。这是第一份有关医生警告流感爆发的记录
[2]。虽然我
们尚不能确定,但哈斯克尔也许是1918年流感疫情在 美国乃至全世界
的着地点。
哈斯克尔以东300英里,是美国陆军所在的芬斯顿营地(Camp
Funston)
[3]。来自营地的士兵在流感疫情高峰期看望了位于哈斯克尔
的家人,并于1918年2月底返回基地。3月4日,芬斯顿营地的第一名士
兵患上了流感。随着士兵在芬斯顿营地以及其他军营和非军事领域之间
自由行动,病毒呈波浪形向外扩散
[4]。它首先抵达法国布雷斯特
(Brest),美军最大的登陆点
[5]
,并在该地进行传播。这些事实有力
地支持了1918年全球流感疫情源于美国中心地带的预测(但这只是一种预测)。
证据表明可能还有另外两个着地点。第一个是在法国。来自伦敦大
学的病毒学家约翰·奥斯佛(John Oxford)注意到,1916年,法国北部
埃塔普勒(Etaples)的英国军营暴发了一场流感。两个月后,在英国军
队的总部,位于英国奥尔德肖特(Aldershot)的一个军营爆发了几乎同
样的流行病,其中四分之一的患者因病死亡。医生注意到这场流行病与
法国暴发的流行病有诸多相似之处。两年后,奥斯佛指出,在很短的时
间内,有报道称在相隔很远的国家爆发了流感疫情。1918年9月至11月
[6]
,挪威、西班牙、英国、塞内加尔、尼日利亚、南非、中国和印度尼
西亚都受到了疫情的影响。当时国际航空旅行还没将世界连接起来,那
么病毒是如何得以迅速传播的呢?奥斯佛推理认为,肯定很久之前病毒
已“根植”于这些地方,也许是由1916年冬季第一次世界大战高峰期间返
回欧洲的士兵带回来的。
1918年流感病毒是源自法国的埃塔普勒营地还是其他地方,比如堪
萨斯州?约翰·奥斯佛拿出一组法国士兵与活猪、鸡和鹅接触的照片
[7]。他认为罪魁祸首是这些家禽,但这并不能证明它们就是病毒的来源。
病毒也有可能来自世界另一侧的中国。
1918年6月,《纽约时报》报道称“一种奇怪 的类似于流感的流行病
正席卷中国的华北地区。
[8]”报道称大约有2万例新增病例。疫情暴发的
时间比欧洲和美国疫情暴发的时间早几个月
[9]
,但死亡人数相 对较
少。由于之前接触过类似的病毒,人们似乎有了一定的免疫力。是1918
年流感的前身已经在中国传播了好几年然后发展成为全球流行性疾病的
吗
[10]?从中国到法国,肯定有病毒传播的途径。在战争期间,超过14
万名中国劳工被招募到法国
[11]
,许多人驻扎在蒙特勒伊(Montreuil)
附近,距离英国军队的埃塔普勒营地
[12]
不足7英里。在全球范围内,人
类大规模的迁移,对于活跃的病毒来说是个好消息。在1918年,随着欧洲战争进入第4个年头,许多国家对新闻报道进
行了审查,特别是那些有关流行性疾病的报道。有关战争的诸多坏消息
却没有进一步使焦虑的公民和士兵消沉。整个战争期间,西班牙仍然是
一个中立的国家,因此其媒体可以自由报道新的流感疫情。这使人们认
为迈纳博士的“性质未确定的疾病”就是从那里传播的。虽然今天的科学
家仍然在梳理病毒起源理论,但至少所有人都同意一点:所谓的“西班
牙流感”的最早暴发地肯定不是西班牙
[13]。
那么,1918年的病毒从哪里开始的呢?是从哈斯克尔,法国还是中
国?知道这一点可能有助于防止将来暴发类似的疾病,但我们仍然没有
弄明白病毒究竟是从哪里开始的。每一种理论都有证据支持,但随着
1918年流感大流行逐渐淡出历史,我们不太可能得出明确的结论。这种
变化、这种不确定性、这种神秘感是流感危害人类的特征。
与病毒的起源和传播路径一样重要的是有关病毒破坏性的细节。人
们尚未研发出治疗流感的方法或对抗流感的抗生素,而且流感带来的后
果极为严重且难以预测。这种病毒是如何传播的?它具备什么能力?我
们从血腥的欧洲战场上可以找到这两个问题的答案。
病毒发起了两波攻击
[14]。第一波攻击开始于1918年春天,当时有
超过11万名美军士兵被调遣到欧洲战线。自英国向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
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年半。战争席卷了整个欧洲。伍德罗·威尔逊
总统在1914年宣布美国会严格遵循“中立”政策。但随着德国潜艇瞄准了
美国船只,这种局势越来越难以维持。从1917年开始,美国陆军带着大
批年轻人穿越大西洋来到大型的狭窄营地。这些营地为流感病毒的传播
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至1918年夏天,这种拥挤不堪的局面极具致命性。
流感已经发生变异,年轻人尤其会有患病的风险。在巨大的病房里,士
兵们躺在那里彼此触手可及,隔开他们的只是一张悬挂着的床单。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感染率相同的情况下,入伍士兵的死亡人数远远多于平民。大多数生病的士兵被转移到这些拥挤的病房。在那里,又
繁殖出了一种细菌
[15]
,这种细菌能衍生致命的继发性感染。这些病房
非但不能让患者恢复健康,反而成了繁衍疾病的大型培养皿。
美国第16 综合医院红十字会病房,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1918年
病毒不只在营房和船上的医务室传播。在欧洲,成千上万的人在家
乡、军营、码头和战争前线之间来回穿梭。美国战争部门每月向法国派
遣20万人。到了夏天,在欧洲作战的美国士兵就有100多万人。
我们不知道在流感第一波攻击中有多少平民患病之后死亡。当时,对医生报告有关流感的情况,没有做任何要求。已成立的国家或地方卫
生部门很少,而那些现存的机构往往管理不善。但是,通过查看军方保
存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对当时发生的情况有所了解。从1918年3月开
始,堪萨斯州的芬斯顿军营内的流感病例突然增加。在卧床休息并服用
阿司匹林后的两三天,大部分士兵病愈。但有200人感染了肺炎,其中大约有60人死亡
[16]。在一个拥有4.2万人的庞大军营中,这些数字并不
足以引起军医的注意。
欧洲的情况更加糟糕。一名医务人员注意到,他所在的部队流感肆
虐,以至于士兵们无法行军
[17]。到了春天,美国第168步兵团大约90%
的士兵患有流感。到1918年6月,流感已扩散到法国和英国部队。返回
英国的英国士兵中,患有流感的病例超过了3.1万人
[18]
,比5月增加了6
倍。报道称,在欧洲大陆,20多万名英国士兵无法参战
[19]。病毒继续
通过海路进行传播。8月,英国轮船抵岸后,200多名船员罹患流感或患
流感后恢复。之后,病毒袭击了塞拉利昂的弗里敦。在不到一周的时间
里,病毒已经在陆地上蔓延;在9月底前,当地约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已
经感染病毒,其中有3%的人死亡
[20]。在孟买、上海、新西兰有关疫情
暴发的报道也开始见于报端。
第一波疫情有些温和。虽然有许多人患病,但疾病只持续了两三
天。几乎人人得以康复。像通常,婴幼儿和老年人感染病毒的风险最
大,死亡率远高于一般人群。但是,通过检查死亡记录,流行病学家注
意到,青年人和中年人的死亡率呈上升趋势,死于流感的比例较高。
当绘制流感死亡人数与年龄的关系曲线图时,我们最常见的是U形
图。U形图中的一臂代表婴幼儿,另一臂则代表老年人。在这两个年龄
段之间,死亡人数很少。1918年早期的流感死亡曲线图形状呈W状。两
端的死亡率仍然很高,但代表青年人和中年人的曲线也在升高。受影响
最严重的人群,年龄在21岁至29岁,通常情况下这群人被认为最不可能
死于传染病。这一现象很奇特,也令人震惊。依据年龄段划分的流感和肺炎的特定死亡率,包括1911-1915年流感大流行期间(虚线)和
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期间(实线)的死亡率。特定死亡率是指各个年龄段人口中每10万人的
死亡人数。
[21]
当欧洲大陆遭遇第一波流感袭击时,流感在美国几乎消失殆尽。随
着时间的流逝,在欧洲,感染流感的人数也在减少。到1918年7月,《英国医学杂志》称流感已不再对人类构成威胁
[22]。但在大西洋两
岸,最糟糕的情况却即将来临。
————
也许病毒已经变异成一种更致命的形式。也许是秋天拉近了人们之
间的距离,所以他们更容易相互感染病毒。无论如何,另一波流感开始
了。
有关第二次流感浪潮的最早的报道来自波士顿以西约30英里的德文
斯(Devens)营地
[23]。该营地能够容纳约3.6万名士兵,实际驻扎的士
兵已超过4.5万人。疫情始于9月8日左右,并迅速蔓延。每天有90名患
者来到营地医务室就医。之后,这一数字增加至每天500名,1000名。医务室很大,可以接待多达1200名患者。但很快,医务室的空间就明显
不足了。最终,它收容了6000名流感患者。一张床挨着一张床,一排接
着一排。
“我们吃饭、生活、睡觉、做梦都离不开病毒,更不用说每天有16
小时在吸入病毒。”一位年轻的医疗勤务兵在标有1918年9月29日字样的
信中写道
[24]。他被分配到一个150人的病房,而他的名字,罗伊
(Roy),是我们知道关于他的全部材料。流行性感冒(Grippe)——
流感的另一个名字——是所有人都可以思考的事。一个超级营房很快变
成了太平间,穿着制服的死亡士兵被摆放成两排。专门的列车有计划地
将死者运走。连续几天都没有棺材。罗伊写道,堆积起来的尸体“让人
感到疾病的凶残”。这位勤务兵目睹了无数人的死亡,他描述了罹难者
的遭遇。虽然这次的疾病始于另一流感病例,但这次的感染迅速发展成
为“从未见过的最严重的一种肺炎”。营地每天约有100人死亡,其中包
括“无数的”护士和医生。罗伊写道:“这比战后法国的衰败场景更加凄
凉。”他目睹过破坏力巨大又混乱的一战,但与疫情的破坏力相比,一
战的破坏力显得有些逊色。流感疫情更加糟糕。
密歇根大学医学院的著名医生兼院长维克多·C.沃恩(Victor C.
Vaughan)提供了另外一位目击者对德文斯营地大屠杀的描述。在他的
回忆录中,他记录了萦绕在脑海的可怕的场景,“我想清除并毁掉这些
记忆,但这超出了我的能力。”其中一个回忆录与德文斯营地分院有
关。他写道:“我看到数百名身穿制服的年轻、强壮的男子按10人或更
多人一组来到医院的病房。”“他们被安置在婴儿床上,直到每张床都睡
满了人,还有其他人挤进去。他们的脸色青紫,痛苦地咳嗽,然后咯出
了带血的痰。早上,尸体像薪柴一样堆积在太平间周围。”沃恩为自己
无法治疗瘟疫而感到惭愧。他总结道,“这种致命的流感,”“证明在破
坏人类生命方面,人类的干预毫无作用。”
[25]疫情开始不到一个月后,德文斯营地的流感疫情已经导致1.4万人
患病,750人死亡
[26]。流感也席卷了其他军事基地。比如,新泽西州的
迪克斯营地(Camp Dix)、堪萨斯州的芬斯顿营地(Camp Fuston)、加州和佐治亚州的营地。在纽约的厄普顿营地(Camp Upton),将近有
500名士兵死亡。流感于9月12日由2名服务员传播到爱荷华州的道奇营
地(Camp Dodge)。6周后,该营地有1.2万多名男子被感染。医务室一
度容纳了8000多名患者,是其最大容量的4倍
[27]。
每个营地暴发的疫情都遵循一种模式。首先,只有少数人患病,这
些患者与常规流感季的患者没有区别。接下来的几天内,病例呈指数级
增长,会有数百人感染,有时甚至数千人。在3周内,医务室人满为
患,死亡人数在增加。5-6周后,瘟疫就像它到达时一样神秘地消失
了。一些患者患有肺炎,但没有新增病例,生活慢慢恢复正常
[28]。
由于军方的需要而保存下来的记录,让人们对军营暴发的流感有了
更多的了解。但第二波流感不但袭击了军营,也导致美国各城镇数万人
殒命。这一波流感的综合杀伤力更具挑战性。当这波流感在1919年春末
消退时,美国平民和服务人员的死亡人数达到了67.5万人
[29]。巨大的
死亡人数令人震惊,疾病的传播速度令人无法想象。几乎每个城镇都受
到了疾病的冲击。
————
1918年,费城的人口超过170万。就像20世纪初大多数正在发展中
的城市一样,费城居民大多居住在狭窄的公寓里。他们特别容易感染流
感,因为费城的大多数 医生和护士都在国外,往往都受过伤并且厌
战。随着流感来袭,留在城镇的少数医疗专业人员因为劳累而身体瘦
弱。他们没有为即将发生的事做好准备。
流感可能于1918年9月中旬传播至费城,当时报纸报道称病毒正从军营向平民社区迈进
[30]。有传言说是德国装载细菌的潜艇导致了疫情
的暴发
[31]。事实并非如此,罪魁祸首很可能是费城海军造船厂。
该船厂有4.5万名船员并发展成为美国最大的海军基地。1918年9月
7日,该基地接待了300名从波士顿换乘的水手。很可能其中一些人身上
潜伏有流感病毒。2周后,900多名船员生病了。基地官员在讲话稿中写
道: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流感只不过是以新名字
[32]
伪装的平常的季节
性细菌。
但这种病毒即将在很大程度上向平民发起攻击。在病毒传播方面,战争债券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1918年4月,纽约市
举行了一场巨大的自由债券大游行。电影明星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
(Douglas Fairbanks)向肩并肩的游行群众发表讲话。凭借出众的外表
和迷人的个性,他号召群众购买债券以支持战争。5个月后,费城也加
快了敦促群众购买债券的步伐。《费城问询报》(Philadelphia
Inquirer)的一篇文章称
[33]
,该市计划在9月28日星期六为第4次自由贷
款运动的发起举行盛会。预计会有3000名战士参加,“如果需要的话,还会有女性士兵参与该活动”。数百名工人和司仪将与他们一起参加这
个活动,他们会让群众一起唱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流感疫情肆虐期间
进行的。有人担心如此大规模的聚会会促进流感的蔓延,但这种担忧被
人们的爱国热情所淹没了。
战争债券游行活动本质上是流感的行进乐队。当大量的群众沿街观
看并不断欢呼时,海军军人们也来到了百老汇街。
“这是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盛会,”
[34]
《问询报》称,估计有10多
万人聚集在街道上。随着人们伸展脖子以便看得更清楚,他们也顺带把
流感病毒传染给了别人。自由债券大游行活动实际上释放了这种病毒。
辉煌的游行刚刚过去两天,每天就有100多人死于流感。在短期内,这些数字增长了6倍。卫生官员每天都宣布疾病已经过去了,不料
下一次又发布了更严峻的统计数据。费城公共卫生部部长威廉·克鲁森
博士(Dr.William Krusen)下令关闭学校、教堂和剧院。如果他禁止自
由债券游行,情况也许就不会变得那么糟糕。各处张贴的布告提醒大家
不要在街上随地吐痰。但这并没有起多大作用。仅在一天的时间内,就
有60名随地吐痰的人被逮捕。
海军档案馆
由于生病人数过多,法院和市政办公室关闭,其他基础服务机构因
为没有了员工在苦苦支撑。警察和消防部门因人员减少而难以正常运
转。由于严重缺少员工,宾夕法尼亚州贝尔电话公司(Bell Telephone
Company)宣布只能处理那些“疫情或战争所需”
[35]
的服务电话。由于
正规医院超负荷运行,费城还创办了一所急诊医院。一天之内,500张床位都住满了病人。克鲁森呼吁人们保持冷静,并告诉公众不要因夸大
的报道而感到恐慌,但费城正遭受瘟疫的蹂躏,又有谁能做到处乱不惊
呢?
费城唯一的公共太平间只能容纳36具尸体。但这所太平间很快就堆
了数百具尸体,大多数尸体只覆盖着血迹斑斑的床单。每弄到一副棺
材,就有十具尸体在等候着。死尸散发的恶臭无处不在。当地的木工放
弃了正常的生意,开始专职做棺材。一些殡仪馆的收费标准增加了
600%以上
[36]
,导致该市将增长上限设置为“只有”20%。
在10月中旬,费城的死亡人数达到了顶峰,然后,瘟疫几乎与它来
临时一样突然消退了。当然,流感仍然存在,但因流感死亡的人数回落
至以往的水平。这个城市慢慢恢复了以前健康的模样。
费城发生的疫情在美国和世界各地重演。在旧金山,流感在10月也
达到顶峰。当月有1000多人死亡
[37]
,几乎是平常死亡人数的两倍。流
感向阿拉斯加的朱诺(Juneau)传播。该市试图通过强制检疫来阻止疫
情蔓延2
[38]。州长下令所有下船乘客必须接受码头医生的检查。任何出
现流感症状的人都不许进入朱诺。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阻止那些携带
病毒但尚未出现流感症状且看起来依然健康的人进入。几天后,这些病
毒携带者离开西雅图并停靠在朱诺码头,他们仍处在流感的潜伏期内。
当他们抵达码头时,由等待的医生对其进行简要的体检。如果医生发现
他们没有流感的征兆,就允许其进入朱诺。这是病毒潜入的最可能的方
式。病毒从朱诺传播到诺姆(Nome)和巴罗(Barrow)以及居住在数
十个偏远村庄的美洲原住民。与其他地方相比,流感在部落内的破坏性
更强。这些部落与其他人群处于自然分离状态,因此缺乏流感抗体。在
1918年流感暴发期间,位于阿拉斯加西部,拥有300名人口的小镇威尔
士(Wales),有一半人丧生。在布雷维格(Brevig Mission)的小型聚
居地,居民有80人,但只有8人幸免于难。1918-1919年纽约、伦敦、巴黎和柏林的流感死亡率曲线
[39]
从长远来看,北极圈附近发生的 这些恐怖事件有助于人们在不久
的将来对抗这种病毒。死者被埋在寒冷的土地中。这个永冻层安息地,掩埋并保存了死尸,使得80年后的科学家们能够提取1918年病毒的样
本,并首次确定其遗传密码。但在当时,这些尸体还在等待,冻结在泥
土与时光中。
————
美国此时正在打两场战争。第一场战争是针对德国及其军事盟友。
第二场战争是针对流感病毒及其细菌盟友。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这
是一场针对细菌和德国人的斗争
[40]。
随着盟军在西部战线上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流感袭击了运送部队到
欧洲战壕的船只。在法国东北部的阿贡森林战役(the Battle of ArgonneForest)中,流感夺去了许多美国远征军士兵的生命。正如大战几乎笼
罩着欧洲每个国家一样,流感在整个欧洲大陆肆虐。在一个拥有1000名
新兵的法军基地中,有688人住院治疗,49人死亡
[41]。巴黎关闭了学
校,但剧院和餐馆却没有停业。尽管有4000名巴黎人死亡
[42]
,咖啡馆
仍在开放。流感越过了战壕线。德军也深受其害。“每天早上都必须听
取工作人员报告流感病例的数量,以及他们对如果英国人再次发起袭
击,德军存在什么劣势的抱怨。这是一件使人痛苦的事情。”
[43]
当时,一名德国指挥官写道。
在英国,这是一种“保持冷静并继续生活下去”的方式。我在伦敦出
生并在伦敦长大,即使现在大部分时间我居住在英国以外的地方,我也
知道要面对逆境咬紧牙关,这是我童年时就明白的道理。当祖母回忆起
1940年德国空袭伦敦期间从伦敦撤离的场面时,我曾在她的脸上看到过
这样的镇定、沉着。我认识到这是对上一代西班牙流感的反应。“保持
冷静并坚持下去”不仅是公共行为的一种指示,也是英国文化基因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
起初,报纸几乎很少谈及这种流行病,如果一定要谈,报纸会把这
些报道埋在内页。英国政府和富有同情心的媒体默认限制任何有关流感
的讨论
[44]
,目的是避免削弱公众士气。因为世界大战已经进入第4个年
头,人们已经厌倦了战争。对事实进行如实报道和维持士气之间的紧张
关系,在J·麦克奥斯卡(J. McOscar)博士写的一封信中有所体现
[45]。
这封信隐藏在《英国医学杂志》的最后部分。
“无论男人、女人,还是孩子都有亲人离世的惨痛经历,我们现在
经历的黑暗日子还不够多吗?”他写道,“如果在发布此类报告时能够更
谨慎一点,而不是尽可能多地收集让人沮丧的消息来扰乱我们的生活,这样岂不会更好?一些编辑和记者似乎应该休假。他们去休假越早,对
公共道德也就越好”[原文如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刊发这封信的刊物在同一期的头版刊登了一份
长达5页的有关流感的详细报道。该报道强调了大流行性疾病的破坏
性。报道指出,英国和法国军队暴发了灾难性的流行病
[46]。该流行病
横扫了整个军队,致使军队丧失了战斗力。
英国的首席医疗官似乎也不愿意打扰任何人的生活。他的建议很有
限
[47]
:戴上小口罩,吃得好点,喝半瓶低度葡萄酒。英国皇家医学院
(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并宣布该病毒不
再像往常那样具有致命性。在这一连串的事件中,英国人似乎无动于
衷。1918年12月,随着大流行性疾病的结束,《伦敦时报》评论
说,“自黑死病以来,没有哪场瘟疫像这场瘟疫这样席卷了全世界。也
许,从来没有哪场瘟疫比这场瘟疫影响的人更多。”
[48]
那年早些时候,《泰晤士报》的医学记者夸大其词地描述了这样一
个民族,他们“高兴地期待”
[49]
着流行疾病的到来。历史学家马克·霍尼
斯鲍姆(Mark Honigsbaum)认为,英国政府故意鼓励这种坚忍主义,努力培养国人蔑视德国敌军,同样蔑视暴发的流感。
无论英国人对这一大流行性疾病持何态度,在这场流行病中伤亡的
人数都是巨大的。当流行病消退时,超过四分之一的人被感染,有超过
22.5万人死亡
[50]。在印度(当时属于英国领土),流感更具有致命
性,死亡率高于英国10个百分点,印度军队的死亡人数是英国军队的2
倍,一共有大约2000万印度人因流感大流行而死亡
[51]。
接下来是澳大利亚、新西兰、西班牙、日本以及整个非洲国家。所
有人都遭受了苦难,全世界共有5000万至1亿人因流感而死亡,人们对
近乎世界末日的猜测感到无比的恐惧。在大规模死亡之后,当公众关
心“这场流行病是如何形成的?”和“多少人受害?”时,科学家们不禁要
问:“为什么?”是病毒本身,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导致流感具有如此大的杀伤力?我
们已经找到了致使这么多人死亡的4种不同的解释。每种解释都有一些
证据支持,但没有一种解释是完全令人信服的。
第一种解释是
[52]
,病毒表面有一种蛋白质可以阻止干扰素的产
生。该干扰素向我们的免疫系统发出信号,表明我们的防御系统已被渗
透。将氧气转移到血液中的健康肺细胞,被病毒劫持,并在病毒复制过
程中遭到破坏。一旦这些健康的肺细胞死亡,它们就会被无法输送氧气
的暗淡的纤维状细胞所取代,就像在切割口部位形成的疤痕一样,看起
来与周围健康的皮肤不一样。几个小时内,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名叫罗
斯科·沃恩(Roscoe Vaughan)的美国陆军士兵被尸检。尸检表明他的肺
部有这种类型的肺炎。干扰素的破坏有可能使1918年的病毒引发致命的
病毒性肺炎。
第二种解释是,如果1918年的病毒本身不能致人死亡,那么继发性
细菌性肺炎可能会杀死人。大流行性疾病患者的身体变得虚弱,他们的
肺部已经被破坏,会感染链球菌(streptococcus)和葡萄球菌
(staphylococcus)等。在抗生素尚未研发出来的年代,这种情况是致命
的。我们现在认为,1918年大流行中的大多数患者是由这些继发感染导
致死亡的,而不是流感病毒本身。南卡罗来纳州士兵的肺提供了这种感
染的证据。他死于病毒的连续攻击,以及伴随着身体防御体系崩溃而至
的细菌感染。
对1918年流感杀伤力的第三个解释是,流感病毒引发了过度的免疫
反应,这种反应开启了对身体的自抗。假设你割伤了手指,细菌入侵并
感染伤口。由于血液流量增加,你的手指会肿胀、发红、变热,从而提
供更多白细胞来对抗细菌。其他类型的细胞因子信号蛋白会对这种对抗
感染的痛苦但必要的过程进行调节。一旦克服了这种感染,细胞就会停
止生产细胞因子,并且免疫系统会恢复以往的警惕状态。许多1918年的流感患者没有恢复正常。他们的肺被“细胞因子风
暴”(cytokine storm)
[53]
——过量生产的信号蛋白所击中。在细胞因子
的繁荣期,它们开始入侵并摧毁健康的细胞。当细胞因子风暴来袭时,免疫反应就会失控。细胞因子风暴激活了更多的免疫细胞,免疫细胞释
放出更多的细胞因子,细胞因子又激活更多的免疫细胞,这种循环周而
复始。大量的液体从饱受战争蹂躏的人们的肺部涌出。肺部的健康气囊
结痂。呼吸变得越来越难。
目前还不清楚为什么这场风暴发生在一些患者身上而其他患者却没
有,或为什么在20~40岁的人群中更为常见。传染病专家称这是本次大
流行最大的未解之谜
[54]。如果我们能够解开这个未解之谜,或许能够
保护自己不受另一种致命的流感瘟疫的伤害。
第四个解释指向了与流感传播有关的环境。它由一种源于鸟类的新
型病毒引起。在对人类构成威胁之前,病毒先在另一个宿主(可能是猪
或马)身上寄宿一段时间。当人们同时生活在一起——住在公寓或军营
里——并且异常流动的时候,病毒开始对人类的健康构成威胁。因为大
战使受感染的士兵们不断转战于欧洲及其他地区。工薪阶层家庭共用床
铺。士兵们并排睡在婴儿床上,并且乘坐统舱船环游世界。如果没有人
类这些行为,流感病毒无论多么致命,都不会如此迅速地传播。
今天,流感致死率不到0.1%。几乎每一名患者都可以康复。在1918
年流感大流行中,大多数患者也都康复了,但死亡率却比以往高出25倍
[55]。在美国许多人死于1918年的大流行性疾病,当时人们的平均寿命
从原来的51岁降至39岁
[56]。1900-1960年美国人均寿命的变化,显示了1918年流感大流行的影响
[57]
1918年12月,在疫情中期,1000名公共卫生官员聚集在芝加哥讨论
疫情。在三个月内,瘟疫夺走了40万人的生命。有人已经预言,第二年
会暴发会更加致命的流感疫情。
与会者之一的乔治·普莱斯博士(Dr.Georg Price)在他的报告中描
述了当时的现状。读起来令人恐惧
[58]。
首先,医生承认他们不知道流行病的原因。“我们不妨承认是病毒
并称之为‘x’病毒”,普莱斯写道,“因为病毒缺乏一个更好的名字。”医
生们在患者的分泌物中发现了几种不同的微生物,但这几种微生物是致
病元凶还是受疾病磨的身体自身出现的“机会致病性劫持
者”(opportunistic hijackers)?(事实证明是后者)
与会者就一些事情达成了一致意见。传播疾病的任何病毒均能在喉
咙、鼻子和嘴巴的飞溅物和黏液中被发现。借助飞沫,病毒可以通过打
喷嚏、咳嗽以及从手到嘴的接触进行传播。因此,一位医生建议减少病
毒传播的唯一方法是让“每个病人都穿着潜水员的服装”
[59]。医生们也一致认为,如果患者从流感中康复,他就会出现一定程度
的免疫力。许多40多岁的人都幸免于难。当时的理论和现在的一样,认
为那些在1898年经历过严重流感的人,已经具备了针对1918年流感的免
疫力。
但是如何控制疾病呢?由于与会者普遍没有信心,会上展开了激烈
的讨论。尽管采取了预防措施,但流感已经蔓延,然后它突然意外地消
失了。当时大量群众佩戴着面罩,但这并不能保证大家一定能够得到保
护。许多卫生官员认为它们提供了 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这也许是事
实,但无论如何,采取安全措施,仍然有一定的用途。芝加哥的卫生专
员
[60]
明确表示了这一点。“这是我们的责任,”他说,“让人们免于恐
惧。忧虑比流行病更具有杀伤力。就我个人而言,如果人们想要在金表
链上装个兔子脚,并觉得这样能帮助他们摆脱恐惧的生理行为的话,我
愿意帮他们实现。”
官员试图收集患者和死者的数据,但许多州没有被要求报告病例。
疾病前线的医生们过于忙碌,以至于无法填写必要的文件。很多患者在
接受治疗之前就已经死亡。因此几乎无法估计死亡人数,或被感染之后
康复的人数。人们还没来得及计算患者的人数,病毒已夺走了患者的生
命。没有任何机制可以用实际的数字来描述怪异的瘟疫。
在17世纪瘟疫期间,伦敦许多受疾病折磨的家庭在他们的前门上画
了一个大十字架,上面写着“主啊,请保佑这家人”。这个十字架警告着
人们,室内潜伏有疾病和死亡风险。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1918年,但是
以更加规范的方式——把“危险告示”张贴在门前。“危险告示”警告健康
人远离此地,在许多社区,几乎每家的门上都做过此类标记。
在公共卫生方面人们还做过一些努力,通过关闭学校、剧院、商
店,以减少公共场所的拥挤和混乱。这是一种迫使人们在休闲时间睡
觉、储存能量并避免感染的方法。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封闭措施是否奏效。底特律关闭了少量的公共场所,只有相对小面积的地区遭受了流感
袭击。而费城制定了更严厉的封闭政策,却并未有效地阻止这场灾难发
生。纽约卫生局局长罗耶·科普兰(Royal Copeland)改变了公共汽车和
地铁的时间表,以阻止 乘车时人员过度拥挤。他在城市周围安装了大
型标志,提醒公众不要吐痰。但他没有关闭学校和剧院。他认为,与其
让学生住在拥挤的廉租公寓,还不如待在学校里,在学校他们可以学习
如何保持健康
[61]。
普莱斯博士对1918年芝加哥会议的描述以号召人们采取行动而结
束。尽管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绝望情绪,但他坚持认为,结束流感疫
情的最佳方法是借助于公共卫生政策。需要更好地协调各个卫生机构,这些机构应该像军队一样置于统一指挥之下。为了击败敌人,私人和社
区机构需与各级市、州和联邦共同努力。普莱斯知道他是异想天开,而
病毒无所谓。流感的诸多症状中,有一种症状比发烧或呼吸短促更致
命。这是一种无用的感觉,这种感觉对密歇根大学医学院院长维克多
·C.沃恩产生了终身影响。在目睹了这么多人的死亡之后,沃恩决心“再
也不要鼓吹医学院取得了巨大成就,要虚心承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无
知”。
[62]
————
关于1918年流感大流行的历史读起来令人沮丧。这就像看一部恐怖
电影一样。你知道凶手是谁,但你无法进入电影中的场景去拯救受害
者。但是,在大流行性疾病期间和随后的几年中,出现了源源不断的医
学发现,这使我们首次能够对流感进行还击。
一些医疗专业人员非常渴望查明导致流感的原因,他们将自己的生
命置之度外。1918年和1919年之间的那个冬天,在流感疫情高峰期,约
有3000万日本人患病,其中超过17万人 死亡。尽管如此,一位名叫T.山
之内(T. Yamanouchi)
[63]
的教授设法找到了52名主动充当人体实验对象的医生和护士。T.山之内教授从流感患者身上取下“痰液”,放入实验
对象的鼻子和喉咙中。有些人直接接触了这种被污染的液体,还有些人
在通过非常细密、可以过滤掉所有细菌的过滤器过滤后才接触它。这两
群人很快就出现了流感的迹象。于是,日本研究人员据此断言已知的细
菌不可能是造成流感的原因。此外,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这种疾病可以
通过进入患者的鼻子或喉咙来传播,这是我们现在认为理所当然但当时
几乎没有人认识到的流感特征。
一直有研究人员愿意把自己当作实验对象。澳大利亚医生巴里·马
歇尔(Barry Marshall)就是一个例子。他与合作者共同发现了导致胃溃
疡的细菌,被授予诺贝尔奖。为了证明这一点,马歇尔本人喝下了含有
细菌的污泥,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结果他患了胃溃疡。但是1918年的
这些日本志愿者的勇气更加引人瞩目。他们周围的流行病正在以前所未
有的数量夺去患者的生命,并且没有已知的原因或治愈方法。然而,52
名医生和护士同意接种从那些感染者身上提取的材料。他们准备做出最
后的牺牲。他们的勇敢和无私令人难以置信。
日本人的发现很快就被复制了。1920年,两名美国研究人员研发出
一种小型过滤器,可以滤除流感患者洗鼻液中的所有已知细菌。然而,当把剩余的物质注射到活兔体内时
[64]
,仍然能够在活兔身上引起类似
流感的症状。他们得出结论:细菌不是流感的成因。不久,有报道称
[65]
其他疾病是由于洗鼻液剂量太小而无法被过滤器过滤掉的细菌引起
的。流感大流行的原因仍然是一个谜,但我们已经排除了细菌的嫌疑
[66]。
那么,通过那些细菌过滤器人们得到了什么?当然是流感病毒。
1933年,伦敦北部一个实验室(离我长大的地方只有几英里)的两位英
国科学家证实,从患者喉咙里提取并过滤掉所有细菌的样本可以让雪貂
感染病毒。(事实证明,雪貂是为数不多的感染流感的哺乳动物之一。雪貂比猪更容易感染流感病毒。)这一研究是建立在日本人的实验结果
基础上的,英国科学家得出的结论
[67]
是“人类流行性流感主要是受到病
毒的感染”。在同一个十年内,人类取得的另一个重大进步是发现了可
以培养流感病毒
[68]。流感病毒被注入正在发育的鸡胚胎的羊水中,不
料对于相当挑剔的病毒来说这竟是一种理想的生长媒介。这是一项惊人
的重要发现。如果你能够种植病毒,你也就可以收集病毒、杀死病毒或
将其注入健康人群的体内,然后就得到了疫苗。
最后,在1939年,病毒学史上出现了分水岭。新发明的电子显微镜
拍摄了一张病毒图片。在历史上,我们第一次看到了罪魁祸首的样子。
到20世纪40年代,科学家已经分离出两株流感病毒(A株和B株)并开
始检测疫苗。其中一位科学家是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他后来
研发出脊髓灰质炎疫苗。在克里克和沃森于1953年发现DNA之后不久,人们就确定了病毒的各种构建块。之后,病毒学领域开始研发识别病毒
的工具和技术,并根据遗传成分对其进行分类。
医学是诊断和治疗疾病的艺术,也是防止历史重演的艺术。我们从
1918年的流行病中学到了足够的知识吗?已知的经验教训可以预防另一
场灾难发生吗?我们现在知道遇到了什么病毒,但我们能否更好地对抗
这种病毒?几十年后,当下一次大流行性疾病抵达中国香港时,世界再
次受到疾病的考验。
[1] “Influenza. Kansas—Haskell”,Public Health Reports 33,no.14 (1918):502.
[2] J. M. Barry,“The Site of Origin of the 1918 Influenza Pandemic and Its Public Health
Implications”,Journal of Translational Medicine 2,no.1 (2004):1-4.
[3] J. M. Barry,“The Site of Origin of the 1918 Influenza Pandemic and Its Public Health
Implications”,Journal of Translational Medicine 2,no.1 (2004):1-4.
[4] 有关芬斯顿军营流感暴发的整体描述,参见E. L. Opie et al.,Pneumonia at Camp
Funston”,JAMA 72,no.2 (1919):108-113.[5] Barry,“The Site of Origin of the 1918 Influenza Pandemic”;F. M. Burnet and E. Clark,Influenza:A Survey of the Last 50 Years in the Light of Modern Work on the Virus of Epidemic
Influenza ,monograph from the Walter and Eliza Hall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Pathology and
Medicine(Melbourne:Macmillan and Company,1942),70-71.
[6] J. S. Oxford,“The So-Called Great Spanish Influenza Pandemic of 1918 May Have
Originated in France in 1916”,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Series
B:Biological Sciences 356,no.1416 (2001):1857-59.
[7] J. S. Oxford,“The So-Called Great Spanish Influenza Pandemic of 1918 May Have
Originated in France in 1916”,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Series
B:Biological Sciences 356,no.1416 (2001):1857-59. 奥斯佛专门论述了病毒是否起源于中国
的问题。他认为这种可能性虽然不能排除,但“不太可能”(第1859页)。
[8] “Queer epidemic sweeps North China”,New York Times ,June 1 1918,1.
[9] Christopher Langford,“Did the 1918-19 Influenza Pandemic Originate in
China?”,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1,no.3 (2005):473-505;K. F.
Shortridge,“The 1918 ‘Spanish’ Flu:Pearls from Swine?,” Nature Medicine 5,no.4
(1999):384-85.
[10] 肖特里奇(Shortridge)提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至少在中国南方,在最早的流行病学
证据存在之前约50年,人类可能感染了一种类似H1的病毒。”
[11] Langford,“Did the 1918-19 Influenza Pandemic Originate in China?”.
[12] 肖特里奇援引林恩·麦克唐纳(Lynn MacDonald)的观点,称埃塔普勒附近有中国工
人。参见Lynn MacDonald,Somme (London:Macmillan,1984),189-93.兰福德(Langford)
对中国起源理论进行了详尽分析。他的结论是“1918-1919年,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发生了流感疫
情——尽管当时的健康状况普遍较差,但流感疫情在世界其他地方并没有那么致命。基于这一
发现,虽然奥斯佛和其他学者持有不同观点,我们可以认为1918-1919年流感病毒起源于中
国。”(“The 1918 ‘Spanish’Flu”,494)肖特里奇对这一理论持肯定态度:“我相信流感病毒来源
于中国南方,这符合该地区是大流行性流感病毒出现的地区的假设,并且它随着受经济驱动的
人口流动而扩散到广东省以外。”(“Did the 1918-19 Influenza Pandemic Originate in China?”,385.)
[13] 但这一名称已广泛流传。在关于1918年流感大流行的优秀历史著作中,阿尔弗雷德·克
罗斯比(Alfred Crosby)将此次疫情称为“西班牙流感”的次数至少为47次,尽管该书的第二版
于2003年发行。参见Crosby,America’s Forgotten Pandemic。理查德·科利尔(Richar ......
您现在查看是摘要介绍页, 详见PDF附件(2743KB,316页)。